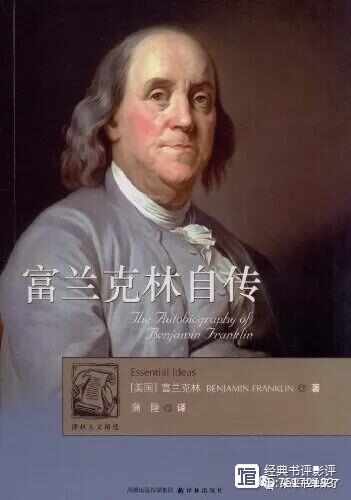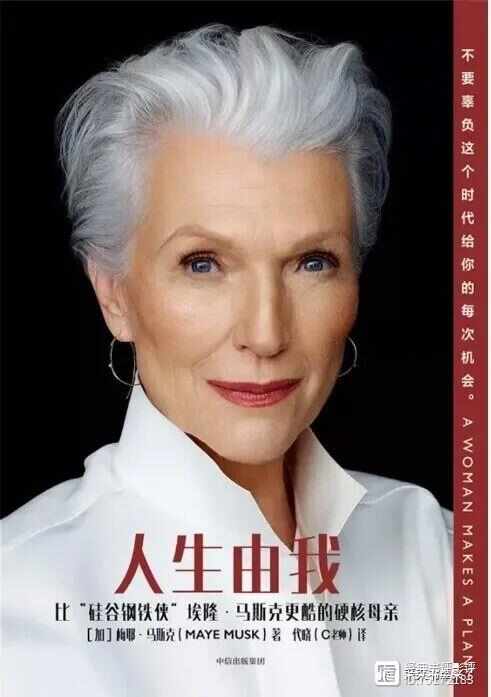从模仿机器到数字有机论:人类引擎的移植

摘自:《劳动乌托邦的消逝》
译|蓝江
第一章:从模仿机器到数字有机论:人类引擎的移植
伴随着21世纪初工业和后工业工作性质的重大转变,用来框定和体现我们所谓的工作性质的隐喻也出现了深刻的危机。一个身体和机器共生的新形象已经出现,历史学家布鲁斯·马斯李希(Bruce Mazlish)恰当地称之为 "第四个断裂"(fourth discontinuity)——-暗指弗洛伊德的三个伟大的虚幻的 "分界线 "或断裂,即人与宇宙(伽利略)、人与动物(达尔文)、人与自然(弗洛伊德)——因为今天对机器的统治已经不再是理所当然的。人们甚至可以更进一步,认为人类机器或人类引擎的隐喻与整个现代历史中工作的转变有着同样的关系,而机器和工业流程本身也是如此。身体作为机器/引擎的隐喻可以被合理地划分为三种简单而不同的历史类型:模仿型、超越型和数字化。其中的每一种,又可以由不同的技术来代表。
18世纪的模仿技术以发条为例,其机械精度能够以非凡的真实性复制某些生物过程。这种人类或动物机器的形式以十八世纪伟大的钟表制造商的手工自动装置为例,如雅克·沃坎松(Jacques Vaucanson)的 "笛子演奏者 "或雅克·德罗兹(Jacquet Droz)的 "写字男孩"。工业革命的超验唯物主义又被转换能量产生运动的引擎所说明:蒸汽机、汽车和泰勒制工人。 今天的数字隐喻从作为新的 "人类机器 "的计算机中获得灵感,并在人工智能、"微观世界 "或 "数字有机体 "方面得到最佳理解。在什么意义上,数字技术可以按照机器或电机的隐喻来考虑?例如,人工智能是能量主义的一个变体吗?我们是否需要一个不同的词汇来描述人类和他们的网络创造物之间的界面,而不是引擎或机器?我感兴趣的不是操作性隐喻本身的这些变化,而是隐喻中的这些变化如何以及是否成为我们谈判人工和自然之间的鸿沟的工具,并唤起工作的生物政治的非常不同的概念。

自动装置的全盛时期是18世纪,当时技艺超群的工匠们为他们复杂的机械装置赋予了如此精致的动作,他们似乎在嘲笑生活和技术之间的界限。其中最著名的是沃坎松,他在28岁时就一夜成名。1738年,他以一个能够精确吹奏长笛的真人大小的小动物震惊了巴黎,以至于难以置信的观众指责他在小动物身体里隐藏了一个小音乐家。随后,沃坎松推出了他最著名的作品,一只机械鸭子,它拍打着翅膀,啄食食物,喝水,并在通过消化系统后排泄出一个腥臭的颗粒。沃坎松的非凡的排泄鸡(连同他的长笛手和机械鼓手),成为一个受欢迎(和商业上的成功)的景点,1742年在伦敦的国王剧院吸引了 "惊奇的观众",两年后在德国巡回演出。沃坎松将他的表演模拟与感知和教学目的相结合--说明一个生理学原理(消化是通过化学过程而不是通过粉碎食物发生的)。然而,无论他如何 "努力使其模仿活体动物的所有动作",沃坎松都没有将生命与机器联系起来。他知道鸭子实际上并没有将食物转化为大便,但正如杰西卡-里斯金所观察到的:“即使他作弊,他的不诚实也是为了服务于真实性,而不是美德;使机器在最朴实的意义上显得栩栩如生。”他的沉默表明他明白,尽管他的鸭子可能模拟生理功能并说明一个自然原理,但它永远不可能达到“自我运动的力量”,即生命。
这些模拟物不仅仅是模型;它们努力 "不仅要模仿生命的外在表现,而且要尽可能地遵循产生这些表现的机制。" 自动机既是认识论上的机器,也是生物力学解释模式的功能说明,同时也是表演性的模拟,似乎体现了自我移动的力量和生成的能力,这一点不可避免地避开了它们。将自动装置置于表演性和教育性之间,表明了作者自己对这些奇妙的机器的矛盾心理。
自动装置也是铭文和模拟的结合,这些技术可以在机器中 "书写 "或 "铭文 "实际的文字(如写字的男孩)或声音(如吹笛子的人),这些机器复制了我们的感官设备的效果,同时又具备了它的外部形式。正如本雅明告诉我们,模仿不仅仅是通过人工手段对自然的模仿,而是一种能力,是“一种力量的弱小残余,充分迫使我们类似地存在和行动”。在本雅明的技术模仿理论中,无疑存在着神秘主义,这也说明了为什么18世纪自动装置的两个核心方面经常结合在一起:作为科学创造和表演作品,它们的强大吸引力在于其未实现的本体论承诺——自然和终极生命的再现。它们被设计成体现了产生自身运动的能力。
在19世纪,自动装置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一种是对特定生理过程的像生命一样的表现,另一种只是复制其机械效果。后者不再是复制品,而是假体(prostheses),是人类感觉器官的延伸。在他关于声音技术的优秀著作中,詹姆斯·拉斯特拉(James Lastra)得出了这种区分的后果。如果说“古典自动装置”模仿或复制了有机体或肉体的运动,那么19世纪的设备,如留声机和电话,放弃了对模仿的追求,但能够更有效地复制自然,甚至可能比自然本身更完美。这个过程,可能被称为自动装置的去神秘化,大大减少了模拟的幻觉特征,同时完善了声音的铭文,或更准确地说,声音的物质形式。作为模拟物,它们不再需要模仿生命体的属性,而且,从本体论上讲,这种模拟物对构成实验室中正在创造的生命体的“生命”的问题无动于衷。
笛卡尔提出的经典问题,对他来说,无论制作得多么精良,自动装置都缺乏自我运动的能力(灵魂、情感、语言、自发性),因此仍然只是模仿性的生命,仅仅是与生命的对应物,这一点已经变得毫无意义。甚至在更早的时候,在十八世纪,我们已经可以观察到某些对自动物的解密的姿态,甚至在坚定的唯物主义者中。著名的《人类机器》(L'homme machine)(1748)的作者拉美特里承认,生命机器超过了单纯的机器。最后,沃坎松、德罗兹和门采尔(Menzel)的 "经典 "自动装置只能说明他们明显未能体现的自我运动能力的原则。
十八世纪的自动装置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工作机器,尽管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它们确实在做 "工作"。他们的能量(或力量)由他们的创造者提供,同时作为娱乐和生理学原理的例证。可以肯定的是,它们的作者看到了它们的生产潜力,在沃坎松的例子中,让他在1745年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机械织机。
相比之下,工业革命的生产主义受一种非常不同的力的概念所支配,这种概念完全拒绝把 "自我运动的力量 "作为一种幻觉,并认识到人类社会和自然界是由所有生产活动的首要性和最终可交换性(可转换性)联系起来的。随着对热力学原理的理解,一种新的社会想象力出现了,它预示着一种完全不同的引擎隐喻。赫尔曼·冯·亥姆霍兹(Hermann von Helmholtz)是其最热情的推广者,他喜欢指出,热力学定律的发现证明了自动装置的作者无可救药地卷入了他所谓的 "模仿错误"——相信野兽和人体对应的装置 "精力充沛地、不断地移动自己……而且从不上发条。" 自我运动的力量是一种幻觉;所有的生命和机器都是由转化为运动的能量来移动的。
一、劳动力的发现
引擎的隐喻出现在19世纪的前25年。 在萨迪·卡诺(Sadi Carnot)于1824年发现 "热的动力 "之后,人们清楚地认识到,自然界的所有力量在本质上是一种单一的、普遍的能量的不同种类的能量而已。热力学的发现表明,模仿机器是一个认识论的死胡同,因为能量总是普遍存在于所有自然和技术中。
前工业时代的机器与19世纪中期的生产主义不同,它们缺乏一个统一的、超验的隐喻。在牛顿的宇宙中,各种力量(重力、风、水、马)推、拉或转动机器,产生运动。在亥姆霍兹的宇宙中,能量被引擎(自然的、人类的和技术的)转换为工作。与机器的隐喻不同,引擎的隐喻是生产主义的:它不是简单地指运动的机械产生,而是指可计算的、自然的能量转换渠道的工业模式,从自然到社会,再回到自然。借用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的一句话,19世纪能量主义的生产隐喻是以 "不断的转移和转换 "为框架的,而18世纪的劳动概念是在 "创造 "的框架内运作的。工业革命的生产主义受到这样一种认识的支配,即人类社会和自然界是通过所有生产活动的首要性和最终互换性(转换性)联系在一起的,无论是身体、技术还是自然。
如果说18世纪的机器是牛顿宇宙的折射,它有多种力量、不同的运动来源和可逆的机制,那么19世纪的机器隐喻则来自热力学发动机,它是强大自然界的仆人,被视为一个永不减弱的动力库。机器只有在由某种不连续的外部来源提供动力时才能够工作;相比之下,引擎由内部的动态原理调节,将卡路里转化为热量,将热量转化为机械功。因此,身体、蒸汽机和宇宙被一个单一的、不间断的链条所连接,被一种不可摧毁的能量所连接,这种能量在宇宙中无所不在,能够进行无限的变异,但又是不可改变的和不变的。
能量守恒定律赋予了力的概念在解释自然世界时无可争议的首要地位。物理学成为最高的科学:能量定律的发现将工作的概念提升到自然界普遍原则的尊严,而不考虑仆人或任何其他工人的 "道德完美"。亥姆霍兹经常提到他对自然的新理解对工作意义的影响。从机械力到普遍能量的语言的转变,消除了对劳动的精神理解的需要;工作伦理被能量的数量经济所掩盖。他指出:"因此,在机械意义上,"工作的概念已经变得 "与力的消耗相同"。因此,工业时代的新技术产生了一种新的身体形象,它的根源在于劳动能力,它不仅与热力学机器相类似,而且在本质上是相同的: "因此,动物的身体在获得热量和力量的方式上与蒸汽机没有区别,但在获得的力量的用途和使用方式上与之不同。" 亥姆霍兹并没有简单地将生物等同于机器,他将能量转换机器——自动装置的特性移植到身体、工业动力机,乃至宇宙本身。
亥姆霍兹看到了蕴含在自我运动能力理念中的社会愿景:从痛苦的劳动中解脱出来,一个永远无所事事的社会,当然还有不劳而获:“对于上个世纪的自动装置的建造者来说,人和动物就像一个从未上过发条的发条,并凭空创造出他们所施加的力量。他们不知道如何在消耗的营养和产生的工作之间建立联系。然而,既然我们已经学会了在蒸汽机中辨别机械力的这种起源,我们就必须问一问,对人来说,类似的东西是否也是有效的。”自动装置的发明者们设想了一个没有疲劳、没有不满、没有厌恶工作的身体。但他们也暴露了他们对电机如何将营养供应转化为热量,并将热量转化为力量的无知。永动机永远不可能被发现,因为自然界中从来没有产生过新的能量来源。力的转换不仅解决了模仿的问题,而且通过将模仿的机器还原为 "从自身创造能量"的身体的幻觉而取代了它。十九世纪的 "超验唯物主义 "产生了一个强有力的隐喻,即自然、技术和人体都是在相同的力的动态规律下运作的--这种同质性远远超过了将生命过程还原为工业技术的模式。
正如亥姆霍兹所说“当我们考虑动物所做的工作时,我们发现这种操作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与蒸汽机的操作相媲美。动物和机器一样,只有通过不断地提供燃料(也就是食物)和含氧的空气,才能移动和完成工作”。对于那些像亥姆霍兹一样,从工业发电机的角度掌握宇宙的秘密的人来说,生命等同于力,而力是支配宇宙的生理-化学原理。“生命 ”被重新定义为不是指机械运动,也不是指任何与生命有关的东西,而是指推动所有自然界的普遍运动力量所采取的特殊形式。 在工业发电机的工作、前工业化铁匠的重击、花边制造商的精细动作或音乐会小提琴手的精确指法之间,没有本质的区别。大自然成了一个巨大的蛋白质能量的蓄水池,等待它转化为工作。
在引擎出现之前,定义劳动的隐喻是源自古典劳动理论家的生成性活动: 约翰·洛克、亚当·斯密、阿贝·西耶斯,当然还有卡尔·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和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把劳动视为人类学的普遍现象,它既是一种赋予意义的活动,又是一种历史上的构成活动,是历史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劳动的解放是社会和个人的解放,是自由生产和表达的解放。然而,在1859年之后,马克思越来越多地用劳动能力的语言重新构建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之间的区别,作为一种转换行为而不是生成。据恩格斯说,马克思认为发现劳动能力是他最重要的成就。他对这一术语的使用归功于19世纪初分析蒸汽机的法国工程师以及威廉·汤姆森和亥姆霍兹的发现,他们首次使用Arbeitskraft(劳动力)的概念来描述能量如何转化为工作,无论是在宇宙、自然、身体还是技术中。因此,劳动能力变得可以量化,并等同于所有其他形式的劳动力(在自然界或机器中)。
马克思轻易地采用了劳动力的语言,对他来说,劳动力成为历史发展的动力。因此,他把注意力从通过劳动解放人类转移到通过更大的生产力解放生产性劳动上。当马克思不再认为劳动是人类学上的典范活动方式时,当他与新物理学相协调,将劳动力视为一种抽象的量(对劳动时间的衡量)和一种自然力(位于身体中的一组具体的能量当量)时,他就成了一个生产主义者。对于他以前的劳动生成观,解放发生在劳动本身,而从转换的角度来看,解放只发生在劳动行为之外,以缩短工时或减少体力和脑力劳动的形式。
在《资本论》中,劳动力的概念也是对生产中人的能量支出的一种量化衡量: “裁缝和织布,尽管它们是质量不同的生产活动,但都是人类大脑、肌肉、神经、手等的生产性支出......只是人类劳动能力支出的两种不同形式。”或者更引人注目的是: “一方面,从生理学上讲,所有的劳动都是人类劳动力的支出,在其相同的抽象人类劳动的特性中,它创造并形成了商品的价值。另一方面,一切劳动都是人类劳动力在特殊形式和明确目的下的支出。”
到他写《资本论》的时候,马克思已经用劳动力的语言重新规划了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之间的区别,作为一种转换而不是生成的行为。他公认的资料来源是威廉·罗伯特·格罗夫(William Robert Grove, 1811-1896),他在1846年出版的热力学概要《论物理力的相互关系》(On the Correlation of Physical Forces),在英国至少重印了六次。马克思认为格罗夫清晰的讨论证实了劳动能力的概念:“一个人在24小时内所做的劳动量,可以通过检查他体内发生的化学变化而大致得出,物质中的变化形式表明先前行使的力。”
恩格斯也注意到格罗夫的贡献的重要性: “格罗夫——职业上不是自然科学家,而是英国律师——证明了所有所谓的物理能、机械能、热能、光能、电能、磁能,甚至所谓的化学能,在明确的条件下都会相互转化而不发生任何能量损失。”当然,采用格罗夫定理,并不意味着马克思把价值降低到肌肉劳动的产品,或把人降低到能量生产机器的地位。但是,用劳动力代替“劳动能力”这样的模糊术语,使他能够对劳动者与机器的关系进行更复杂的分析,更重要的是(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可以看出),从资本的角度来看,资本和劳动之间实际交换的是商品劳动能力:“自由工人所卖的东西,始终不过是力的支出[Kraftäusserung]的具体、部分的措施;劳动力作为一个整体,大于非常具体的支出。” 正如马克思所解释的: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本上是生产剩余价值,吸收剩余劳动),随着工作日的延长,不仅产生了人类劳动力的退化,剥夺了它正常的、道德的和身体的发展和功能的条件。它还产生了这种劳动力本身的过早衰竭和死亡。”
劳动力是历史的动力,是使其自身被机器取代成为可能的自然力量。只要劳动的物质方面首先变得自然化,最终变得机械化,那么,劳动作为一种创造性的有机现实的解放与生产的物质过程的蜕变之间的区别就模糊了。必要性领域的特点是对能量消耗的调节,自由领域的特点是人类能量从外部约束中解放出来。根据马克思的说法:
在这一领域的自由只能包括社会化的人,相关的生产者,合理地调节他们与自然的交流,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是像自然的盲目力量那样被它统治;并在最有利于和最符合他们的人性的条件下,以最少的精力支出实现这一目标。但是,它仍然是一个必要的领域。在它之外,人类能力的发展本身就是一个目的,是真正的自由领域,然而,只有在这个必要的领域作为其基础,它才能开花结果。缩短工作日是它的基本先决条件。
如果说十八世纪的自动装置是能够模拟运动的拟态机器,那么工作科学则将劳动归结为一个转换的过程。力量的转换总是伴随着某种程度的损失、消耗或能量的减弱。换句话说,能量的转换总是伴随着熵,伴随着所有能量交换中的损失。
克劳修斯的热力学第二定律似乎指出了一个更为消极和潜在的灾难性的生产理论。臭名昭著的“宇宙热寂”(heat death of the universe)假说来自于熵定律,根据该定律,宇宙中的能量最终将达到平衡状态;随着功转化为热,能量的耗散或损失最终导致亥姆霍兹所谓的 "所有自然过程的停止"。事实上,正如伊丽莎白·内斯瓦尔德(Elizabeth Neswald)所表明的那样,克劳修斯本人——像亥姆霍兹和威廉·汤姆森等人一样——提出了一种最终状态的可能性,即能量转化为热,使宇宙处于“永恒的热寂”状态。工作、生产和表演的强大和保护性世界与疲劳、疲惫和最终的生态灾难——全球冰冻——的瓦解秩序相对应,在19世纪的图像中经常被描绘为宇宙学的枯竭和永恒的休息状态的世界末日形象。
为什么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现象,特别是哲学家莱兹克·科拉科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认为,虽然恩格斯热情地采用了能量守恒的第一原则,但他拒绝了第二定律,因为他认为这种“对宇宙的热寂判决”是“意识形态上的危险”,从而逃避了社会主义的破坏性生态后果。可以肯定的是,恩格斯在怀疑“热寂”假说方面并不孤单。当代批评家认为,由于没有采用第二定律,马克思和恩格斯切断了古典马克思主义与生产主义的破坏性生态后果之间的任何可能联系。然而,很明显,如果他们认为宇宙的热寂理论是不可信的,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没有完全拒绝热力学第二定律。事实上,有相当多的证据表明,两人都试图理解“枯竭”、“运动损失”和可破坏性定理的含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可能没有充分探讨第二定律对劳动价值理论的影响,但他们确实对乌克兰医生和社会主义者谢尔盖·波多林斯基(Sergei Podolinsky,1850-1891)发展的这一思路给予了一些关注。从1880年开始,波多林斯基坚持不懈地试图说服马克思和恩格斯相信他尚未出版的《人类劳动和能量守恒》(Human Labor and the Conservation of Energy)一书的相关性,该书声称马克思的劳动和生产理论可以用热力学的语言来表达。恩格斯阅读并评论了以英文出版的 “社会主义和物理力量的统一”的意大利文版本,马克思也很可能阅读了这本书。在其他主题中,波多林斯基关注的是熵,认为人类劳动有能力增加地球上的太阳能数量,从而有可能减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消极影响。他还指出,经济增长的最终限制不仅在于生产关系的桎梏,而且直接在于宇宙,在于熵的物理和生态规律。尽管马克思对波多林斯基的文章做了大量的笔记,恩格斯也承认它是 "一个有价值的发现",但他最终认为,波多林斯基把劳动者看作是 "消耗能量的动物 "的努力走得太远了,他试图为劳动支出找到直接的卡路里等价物是被误导了。
最重要的是,他对波多林斯基关于人类劳动者构成最完美的热力学机器的说法持怀疑态度。恩格斯在1882年写信给马克思: “波多林斯基完全忘记的是,劳动者不仅是目前太阳能的固定者,而且更多的是过去太阳热量的挥霍者。能源储备、煤炭、矿产、森林等的浪费程度,你很清楚,比我更清楚。” 那时,马克思已经病入膏肓,无法再继续讨论这个问题。但毫无疑问,他明白,劳动生产率的空前进步,从自然环境中汲取的物质和能量的巨大增长,以及资本主义对原材料和能源的巨大需求,都必须从热力学和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理解。
继后来的马克思之后,德国社会主义的“衣钵承袭者”考茨基拒绝了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普罗米修斯主义和独裁主义,并采用了马克思关于未来由机器释放的能量带来的愿景。艺术、科学和人类福祉方面真正的生产性劳动只有在缩短工作日的情况下才能实现。考茨基比任何其他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都更多地用生动的语言描绘社会主义的未来: "不是劳动的自由,而是摆脱劳动的自由,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机械的使用越来越有可能,这将给人类带来生活的自由,艺术和智力活动的自由,最崇高享受的自由"。 八小时工作制是社会主义国际最持久的贡献,这并不是巧合。正如考茨基在1892年写道:“劳动是生活的条件。但他们的努力必然是为了把他们的劳动时间减少到足以让他们有时间生活。”
- 0000
- 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