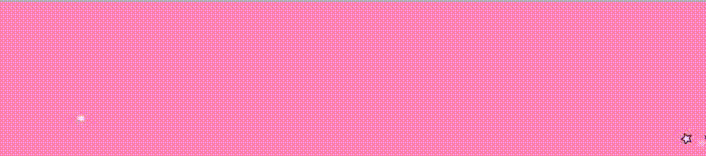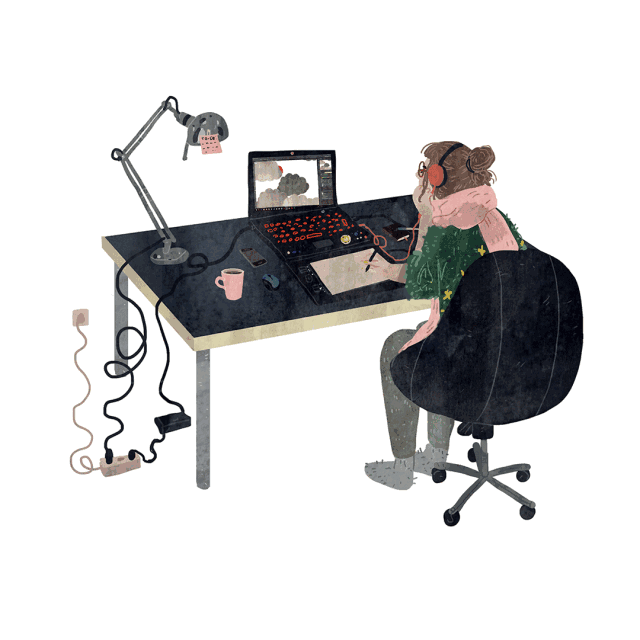妻子重病难愈,陈寅恪提前写下挽联,她苦笑:我定比你活得久
在牛人辈出的中国近代学术史上,陈寅恪先生至今都是神一般的存在。
他是近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也是鼎鼎大名的“清华国学院四导师之一”。
同时代的国学大师吴宓称他是“全中国最博学之人”,历史学家傅斯年有言:“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有趣的是,这位在学术领域造登峰造极的大师,对待个人情感时却是十足的直男态度。
关于娶妻之事,陈寅恪早年公开发表过这样的见解,“学德不如人,此实吾之大耻;娶妻不如人,又何耻之有?”“娶妻仅生涯中之一事,小之又小者耳。”
在醉心学术的陈寅恪看来,娶妻实在算不上是什么人生大事。
也正因为这种婚姻观,1926年,当36岁的陈寅恪从海外留学归来,任教于清华时,年近不惑的他仍未婚娶,甚至没有任何爱情经历。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他情感上的“晚熟”,急煞父母。家人开始还好言催促,陈寅恪却无动于衷。父亲陈立三终于忍不住向儿子发出最后通牒,“尔若不娶,吾即代尔聘定。”
看着父亲着急上火的样子,陈寅恪方觉事态严重,只好请求父亲宽限时日。说来也巧,就在陈寅恪为未知的姻缘正感茫然之际,一幅字画的巧合却为他牵出了天赐的良缘。

那是1928年,同事在与陈寅恪的在一次闲谈中,偶然提及曾在一位女教师家中,看到墙上有一幅悬挂的字画署名“南注生”,他不知“南注生”为何人,特意向学识广博的陈寅恪请教。
谁知陈寅恪听后非常吃惊,沉吟片刻他说:“此人定是灌阳唐公景嵩的后人,住在何处?我要去登门拜访。”
原来南注生便是唐景嵩的别号,唐景崧是曾任台湾巡抚,也是清末有名的爱国将领,曾率军到越南抗击法军。陈寅恪早年读过他的《请缨日记》,对此公仰慕已久。
为此,陈寅恪拜托同事务必帮忙牵线,让他见见这幅字画现在的主人。就这样,陈寅恪后来第一次拜访了唐筼。唐筼正是唐景崧的孙女,彼时正任教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
多年以后,陈寅恪还清晰记得那个春日,唐筼端茶出来招待他们,言笑晏晏,落落大方,她的姿容虽然算不上极美,言谈举止却让人如沐春风。
作为名门之后的小姐,唐筼自幼饱读诗书,是个琴棋书画,无一不精的才女,陈寅恪对她很有好感。
自从那次见面之后,他便常常约着唐筼出来见面,两人谈天说地,交流学问,很快就陷入了“一日不见,思之如狂”的热恋。
这年陈寅恪38岁,唐筼30岁,两人在当时都已属于大龄男女,且都因潜心为学而耽误了婚期,此番相知相识真乃天意。

相识不到一年,他们就在上海缔结了偕老之约,这段水到渠成的“闪婚”也被学界传为一段佳话。
婚后从1929年到1937年这段岁月,是陈寅恪一生中收获最多,也是最幸福稳定的一段时光。
在事业上,因为环境安定,图书资料也容易获取,他发表了约50多篇学术论文和序跋,在国际上声名鹊起。生活方面,妻子唐筼先后为她生下了三个可爱的女儿。
值得一提的是,唐筼在生产第一个女儿的时候,因为身患心脏病,又属高龄初产,引发的感染几乎让她丧命,生产过后,她的身体也大为折损,难以再兼顾工作与家务。
为了保养身体,也为了让陈寅恪能专心治学,不为琐事分心,唐筼这个毕业于金陵女子大学的才女,甘愿辞去工作默默退守在了陈寅恪的身后。这一退,便是一辈子。
彼时的陈寅恪虽然是清华的名教授,薪水不低,但是平日里用来购置书本和资料的支出仍然不菲。加上大哥早逝,陈寅恪还要负担起供养整个大家庭的责任,所以当家的唐筼不得不对家庭用度精打细算。
以前唐筼从未下过厨房。嫁给陈寅恪之后,她特意学做了很多陈寅恪爱吃的湖南菜。为了在节省开支的同时改善生活,唐筼还在清华苑的宿舍里琢磨种了许多菜。
一到夏天,这里就结满了金瓜、葫芦瓜、苦瓜等。新鲜水嫩的苦瓜让唐筼用豆豉就着一炒,满院子飘香。这种恬静安宁的生活让陈寅恪很是满足。

不过唐筼心里一直有个遗憾。那时她已经接连生下两个女儿,很渴望给陈寅恪生个儿子,延续陈家的香火。于是她不顾医生的反对,冒着心脏病和高龄生产的危险又生下了第三个孩子。
第三个孩子,仍是女儿,可是陈家人并不像她想得那么在意。公公还乐呵呵地给孩子起了个好名字——美延,寓意“得众动天,美意延年。”
这让唐筼渴望儿子的焦灼才慢慢平复下来。相比同时代的女子,她自觉幸运,遇到了开明的丈夫和公公。怀抱着初生的女儿,唐筼的脸上绽放出了幸福的笑容。
谁也没想到,这份幸福很快也在接下来的战火中戛然而止。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大举侵入北平。陈寅恪的父亲陈立三作为晚清名仕,忧愤难平。眼看北平就要沦陷,他既不愿做亡国奴,也不愿成为家人的拖累,竟以绝食的方式了断了自己的生命。
祸不单行,在为父亲治丧的时候,陈寅恪突然发现自己的右眼视力急剧下降。到医院检查,发现竟是视网膜脱落,急需入院手术,不然就有失明的危险。
可是手术就意味着,在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他要留在北平休养。当时清华大学已经决定南迁,与北大、南开三校到长沙合并成联合大学。三校师生冒着被轰炸的危险,积极赶赴长沙,陈寅恪也不愿留在沦陷区。
父亲他老人家宁死不屈,他自己又岂能在日伪政权的控制下苟且偷生?于是陈寅恪决定不做手术,即刻离开北平。唐筼虽然很担心丈夫的眼睛,但她更懂陈寅恪的气节。

夫妇俩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他们的大女儿9岁,二女儿7岁,小女儿陈美延尚在襁褓之中。几经艰辛的颠沛辗转,一家人在17天后才抵达长沙。
此后由于时局动荡,他们又去了云南、香港等地。经济的窘迫让一家人居无定所,在四年时间内搬了6次的家。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唐筼和陈寅恪在香港贫病交加,再次陷入绝地,孩子们一个个都饿得面黄肌瘦。其间日本人还威逼利诱陈寅恪出任伪职。
一身傲骨的陈寅恪不肯向日本人俯首,只能携全家仓促逃离香港,最后来到成都的燕京大学临时学校任教,终于又有了一段难得的安静时光。
就在他们长舒一口气,开始平定生活的时候,陈寅恪发现,他仅存的左眼视力也下降得厉害,越发昏花起来。
唐筼认为可能是常年颠沛,丈夫研究任务又重,缺少营养导致的过度劳累。于是她把自己最好的一件旗袍当了,买回了一只母羊。每天早晨,她起床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喂羊,然后把羊清洗干净,再给丈夫挤上满满一碗羊奶补养身体。
可惜上天没有怜恤她的苦心。1944年12月12日,就在陈寅恪完成《唐代三稿》最后一篇《元白诗笺事证稿》后,他发现自己的左眼也看不清了。自此他双目失明。
虽然陈寅恪立即在成都做了眼科手术,但是没有成功。半年后,牛津大学向他发出聘任,并邀约他前往伦敦治疗眼疾。
然而,陈寅恪满怀希望而去,却失望而归。在伦敦的两次手术虽然让他的视力有所改善,然而复明却是终究无望。

没人能承受这样的打击,更何况,陈寅恪还是一个著书立文的学者,失去眼睛,无异于失去了半条生命。
就在他要倒下的时候,还是唐筼撑起了他。
为了让丈夫振作起来,唐筼鼓励他以耳代目,以口代笔,勇敢振作起来。陈寅恪为此每天听报纸,练习口述诗作。唐筼就担当了他的书记官,给他读书读报,随时记录他要写的书信和诗作,还协助他找研究的资料。
在此后的三十年里,她是他的眼。
当陈寅恪被人搀扶着回到清华大学时,校长梅贻琦曾劝他休养一段时间。陈寅恪却答道:“我是教书匠,不教书怎么能叫教书匠呢?我每个月薪水不少,怎么能光拿钱不干活呢?”
这就是陈寅恪的国士风骨。而唐筼作为他的夫人,同样是世间少有的女中英杰。
1949年,陈寅恪曾受邀赴岭南大学任教,这一时期,陈寅恪的助手因为身体不适不辞而别。为了不影响正常授课,唐筼就担当起了并不轻松的助教工作,生活、事业两手抓。
孩子们有时候不解,母亲为什么能如此投入地忘我付出,几乎将父亲视作生活的全部目的。唐筼就向女儿们解释:“你们爹爹的学问造诣非比一般,应让他写出保存下来。”

唐筼是陈寅恪在事业上最好的伯乐与助手,而陈寅恪也视唐筼为生命中的第一知己。每完成一部著作,他都请妻子题写封面。向来不轻易赞许别人的陈寅恪,也倾尽笔墨为爱妻写下“织素心情还置酒,然脂功状可封侯”的诗句。
他曾多次对女儿们说:“妈妈是主心骨,没有她就没有这个家,没有她就没有我们。”
是啊,即便在风雨如晦的动荡时代里,唐筼仍是陈寅恪不二的心灵依靠。
晚年,在特殊时代的惊涛骇浪中,信奉“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陈寅恪很快被推上风口浪尖。而唐筼再次伸出干瘦的臂膀,守护丈夫,守护着这个风雨飘摇的家。
那段时间陈寅恪的各种“声明”“抗议书”全部出自她的手笔。因此陈寅恪受到批判的精神痛苦、心灵愤懑,唐筼比谁都能感同身受,也比谁都锥心刺骨。
她深知丈夫的价值,不希望他垮下去,她只能竭力搀扶着、鼓励着,在日渐灰冷的人生旅途中,努力宽慰丈夫,抹开他难展的愁眉,以孱弱的身躯抵挡密集的箭矢,为他争得一片可喘息的空间。
有了唐筼在生活上的照顾、精神上的支持,身残体弱的陈寅恪凭借超人的毅力,在风烛残年完成了八十万字的《柳如是别传》等著述。

1962年,古稀之年的陈寅恪摔断右腿股骨,自此长卧于病榻。彼时的陈寅恪衰弱得只能进一点汤水类的流食。而唐筼也是以羸弱之躯照顾陈寅恪,她自己的心脏病其实也日趋严重。
凄凉无助中,夫妻相对而泣。奄奄一息的陈寅恪自知不久于人世,在极度的绝望悲苦中,他哀叹妻子的不易,命运的不公,并为唐筼留下了生命中的最后一曲挽歌:
“涕泣对牛衣,卌载都成肠断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
唐筼看了只是苦笑着安慰着虚弱的丈夫:“你放心,无论如何,我定会活得比你长,走在你的后头。”
已经为陈寅恪默默抵挡了半生风雨的唐筼,到了最后时刻,仍不忍心让失明的丈夫在孤寂中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事实最终也如她所愿。
1969年10月7日,陈寅恪走了。弥留之际,他一言不发,只是眼角有泪不断流淌。陈寅恪时候,唐筼出奇般平静,甚至没有留下一滴泪。陈寅恪过世后,唐筼曾对人说:“料理完寅恪的事后,我也该走了。”
而她也没有让丈夫等多久。四十五天后,她便追夫而去了。唐筼有严重的心脏病,大半生靠药物维持生命,停药十余日,生命就可结束。
他和她,终于同生亦同死,同欢乐也同愁。

至此,我蓦然想起陈寅恪在青年时代的爱情观。他曾说:“第一,情之最上者,世无其人,悬空设想,而甘为之死,如《牡丹亭》中杜丽娘是也;第二,与其人交识有素,而未尝共衾枕者次之,如宝、黛是也;第三,曾一度枕席而永久纪念不忘,如司棋与潘又安;第四,又次之,则为夫妇终身而无外遇者;第五,最下者,随处接合,唯欲是图,而无所谓情矣。”
按照这样的说法,陈寅恪与夫人唐筼之间只能算是四等爱情。但是他们却足足用了一生去书写了这平凡而又不平凡的第四等爱情,写得力透纸背,大气磅礴,胜却人间无数。
END.
在阅读中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更多名人轶事,文学解读,欢迎关注我的账号@晓读夜话~
- 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