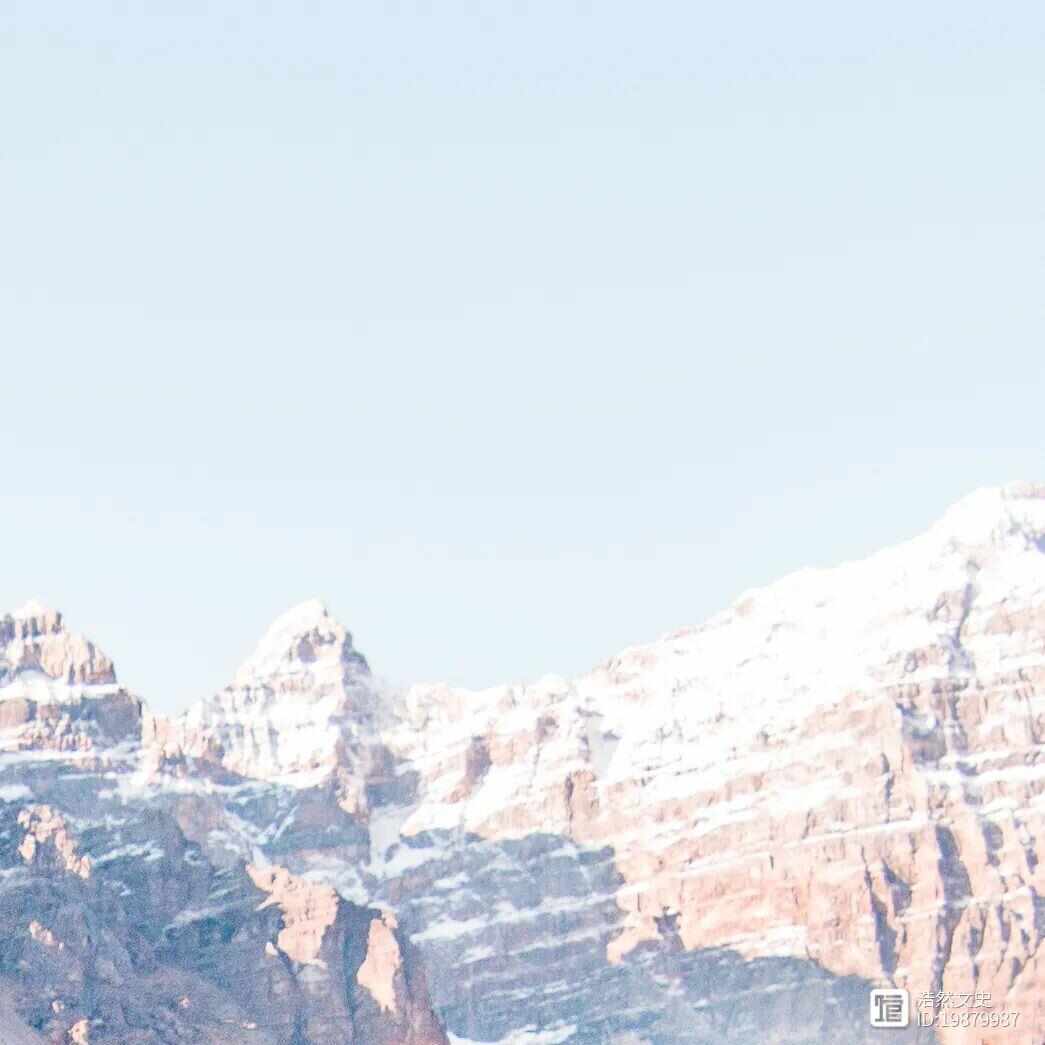川西羌族的毒药猫会害人,都是女人变的,当地人为什么离不开她们

羌族女子
在川西岷江上游的羌族、藏族村寨中,一直流传着“毒药猫”和“毒人”的传说,“毒药猫”利用巫术变成动物害人,而“毒人”则以指甲施毒害人。出人意料的是,这两类群体和中世纪欧洲的“女巫”传说类似,施术者几乎全是女人。当地人非常害怕“毒药猫”和“毒人”,但又不能脱离她们而存在,甚至说出“无毒不成寨”。这是为什么呢?

川西羌族村寨
一、黑夜害人与驱邪仪式:“毒药猫”的相关传说
“毒药猫”是川西羌族地区的一种独特的神话传说。根据川西羌人一般的说法,“毒药猫”被视为害人的妖魔或邪灵,但“毒药猫”本质上不是妖怪,而是一群会变的人,她们基本上是女性,眼睛发红,指甲很长,往往会通过一些法器使用巫术,以变形、附体、恶眼、接触等方式害人。“毒药猫”的神秘法术一般只在女人内部流传,而且也不用特别教授,因为这是遗传性的,女孩一出生便天然具备这种技巧。
“毒药猫”在白天与常人无异,到了晚上躯体睡在家中,灵魂变成某种动物外出害人。每个“毒药猫”都有一个口袋,里面装满了各种动物的毛,当晚上“毒药猫”要出去害人时,就把手伸进口袋之中,摸出一根毛,吹一口气,就会变成相应的动物。

有关“毒药猫”的传说主要来自川西的广袤森林之中,在羌寨山后的森林中有许多野生动物,打猎是羌寨青壮年农闲时期的重要活动。但他们经常会发生意外,据说这是因为森林是“毒药猫”的地盘,“毒药猫”的眼睛十分迷人,能通过眼睛放毒,使人坠入悬崖。更奇异的是,当“毒药猫”变成的野生动物被打伤、打死,村寨中被认为是“毒药猫”的女人也会受伤甚至死去,这更加深了羌寨内对“毒药猫”变身害人这一“事实”的认知。因此,在上山打猎之前,猎人需要烧纸钱以告慰山神或携带白石辟邪,这就是为了躲开“毒药猫”的侵害。
一旦被“毒药猫”投毒,也有相应的解决办法。一是由“释比”、喇嘛或道士主持正规的禳除仪式,二是由个人举行业余的禳除仪式。

个人的驱邪仪式主要是为了避免“毒药猫”的邪气污染。比如,尽量避免到“毒药猫”家中吃饭,不随意向他人泄露自己的行踪以免遭到“毒药猫”的攻击,晚上睡觉的时候把裤子倒放在被子上,等等。
而所谓“释比”,是川西羌寨社会中特有的一种宗教人士,“释比”驱邪的仪式大概也有一套完整的流程:首先是请神、请祖师爷,然后念数段经文逼迫“毒药猫”交出受害者的魂魄,最后由“释比”把“毒药猫”送到一段三岔路口,此时魂魄也回到受害者体内。当然,“释比”也没有彻底消灭“毒药猫”,这种仪式只是一种象征性的举措。他们把象征“毒药猫”的面人捣碎并埋在三岔路口,让“毒药猫”受到众人践踏,暂时镇压了“毒药猫”。但“毒药猫”也能脱身,她们在天亮之前还要回到家中,然后梦醒回到正常生活。
当然,“释比”只是驱离了“毒药猫”,要想真正根除“毒药猫”,还要求助于她们的父母和兄弟。“毒药猫”可能毒害自己的丈夫和儿子,但不会伤害自己的父母和兄弟。因而,在“毒药猫”东窗事发后,经常被父母和兄弟领回娘家加以责罚。既然自己的女儿变成了“毒药猫”,那就要有一个“去毒”的过程。在《羌族故事集》里有一篇“毒药猫改邪归正”,在这个故事中,“毒药猫”往往会“把毒药甩到河头”或“到九条大河里去洗”以“洗净身上所有的毒”。在这个故事的语境中,“毒药猫”的“毒药”似乎又是一种具体性的毒药,这种毒性可以由流动的河水冲洗干净。

释比
二、纯净与不洁:“毒药猫”传说后的族群文化逻辑
除了上述与中世纪欧洲“女巫”相似的邪恶传说,川西的羌寨又认为“无毒不成寨”,也就是说,尽管“毒药猫”是多么遭人厌弃,然而她们还是绵延至今,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避免产生更大规模的瘟疫,“毒药猫”必不可少。为了理解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我们还要深入探寻“毒药猫”传说背后的族群与文化逻辑。
羌族是居住在川西深山峡谷中的居民,通常少则十来户、多则一两百户组成一个“寨”,几个相邻的“寨”,占据一段山沟,组成一个“村”或“大队”。同村的几个寨子通常在婚丧、宗教和经济活动中形成紧密而不可分割的关系。这些“寨”由统一的地盘神信仰所凝聚起来,在较为汉化的地区,这些“寨”又构成了同一祖源的汉姓家族。但对于羌寨村民来说,这种族群划分是根深蒂固的,不止涉及一些神话传说与家族起源问题,而更关注在川西社会中紧缺资源的分配问题。

川西羌寨民居
川西地区山高谷深,自然地理状况恶劣。羌寨村民正是在这种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在半山上开展种植,在深山森林中采药、狩猎、伐木,在牧场上放养马和牦牛。每一个寨都有自己的草场与林场范围,为了保护势力范围,各村、寨都形成了各自的山神或家族神信仰,有时寨中的一个家族或几个家族会形成一个“家门”,祭祀同一家族神,划分领地边界。
正是这样的地理环境、生产方式与社会关系,羌寨内部形成了相当孤立的地域性族群认同。或为争夺地盘,或为解决儿女婚姻纠纷,或为在山神祭祀、庙会活动中相互夸耀,村寨之间经常存在着敌对紧张的关系。对于外界环境的恐惧与自我鼓励,造成了语言文化上的分歧与族群内部的实际划分。
除了这种因争夺自然资源和社会接触关系而产生的敌对与暴力外,对于自然环境的恐惧也促使羌寨村民自我隔离。川西地区自然环境恶劣,山路陡峭崎岖,常有突如其来的暴风雪,而熊、豹子、野牛、野猪更是时时刻刻威胁着上山从事采集活动的村民。村民在晚上都不敢出门,把封闭的寨子作为自己的庇护所,同时,村民又虚构出“毒药猫”害人的传说,以此作为自己的精神慰藉。
我们可以看出,羌寨村民把自己团结在一个个家庭、家族、村寨的认同之中,由各层级的地盘神或山神保护着村民及其地盘。族群边界的纯净与污秽的概念更是把这种孤立状况推到了极致。羌族人以纯净与污秽来区分我族与他族之间的差异,把族群分为汉、羌、藏三部分,或者在藏族中再划分出嘉绒藏族和安多藏族。“纯净”是族群边界的重要标志,汉、羌、藏之间以及羌族内部各村寨之间发生骂战,这种状况为后来女子,尤其是年轻漂亮的女子常被视作“污秽”之物,甚至演变成“毒药猫”埋下了伏笔。

川西羌族村寨
三、无毒不成寨:羌族社会中的虚拟与真实
在“毒药猫”的神话传说中,女子,尤其是未出嫁的女子,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她们扮演了“毒药猫”的主体,而女子最常变的动物就是猫和牛。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编排,与羌族社会中猫和牛的放养方式有关。
在较为汉化的寨子中,牛一般一年四季被圈养在寨子里;而在岷江上游的羌寨中,家牛大部分时间在大山之中放养,自己觅食,自己对抗豺狼虎豹,只有在春耕之时才拉回来犁田。在这种放养方式下培养的家牛大多具有野性,甚至抵触主人。而猫从未被人驯养过,只是与人居于同一空间。它们经常在夜间活动,有时会偷邻家或自家的鸡。无论如何,猫和牛打破了驯养动物与野生动物之间的区分,正如女子打破了内陆人与外地人的区分一样。女子在羌寨中处于边缘地位,且被认为扮演着破坏者的角色。而且,猫在夜间活动,眼睛具有魔力,个性阴柔,猫与“家”的关系若即若离,这些特征都使得猫更具有象征内涵,用猫来称谓女子更为适合。

野牦牛
在羌族村寨中,女子是家中的一分子,也是一个潜在的边缘人。羌人更愿意认为,灶神经常向天神传话告密,出嫁的女子也会把家中的消息告诉给她的兄弟,也就是对于父系氏族而言的“母舅”。在羌寨中一直流传着这样的谚语:“天上的雷公,地上的母舅。”羌人把媳妇的娘家势力比作具有威权的天神,虽然稍显夸张,但也能看出,媳妇经常引入娘家势力,干涉子女的教育、婚嫁及财产分配等问题,“母舅”一方已然成为媳妇赖以对抗父系氏族势力的重要力量。这也就是上文所说的根除“毒药猫”非娘家不可的原因。
而且,羌人也认为,年轻漂亮的女子自身具有的性吸引力也有招致汉人或藏人,扰乱羌族血统纯正的潜在可能性。乱搞性关系这种行为本身被认为是不洁的、罪恶的,这被隐喻为一种“毒”,相应地,从外地嫁来的女子自然就成为替罪羊。女子的年轻貌美成为可能勾引男子、混乱血统的借口,羌族社会本身对外界的敌视与恐惧使得他们产生了对本族群内部边缘人的敌意。

川西羌族女性
回到前面提到的“无毒不成寨”,这指的是如果没有“毒药猫”,寨子里的水就不能喝,寨子里就会发生更大的瘟疫。如果“毒药猫”代表着邻近村寨人群的敌意,那么比“毒药猫”更严重的瘟疫则蕴含着他们对异族人群的畏惧。在这种孤立封闭的村寨生活中,与其他村寨、尤其是岷江上游的那些相对未开化的村寨进行联姻,恰恰是加强双方关系、寻求自保的重要手段。而且,这种“毒”也类似于孟子说的“无内忧外患国恒亡”,强化对”毒药猫”传说的认知也是保持村寨自主性的重要方式。
文史君说
川西羌寨中的“毒药猫”传说蕴含着村寨之间、娘家母舅权力与父系氏族权力之间的矛盾与斗争,这种矛盾具化为不洁与纯洁、女人与男人、女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在社会的骚乱与不安中,女子成为替罪羊。一个社会人群依赖对边缘性人群的打击而获得凝聚力,这种边缘性群体的形成,永远徘徊于历史事实的想象与建构之间。
参考文献
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华书局,2008年。
王海燕,《藏羌彝走廊邪神信仰一体多元的人类学研究》,中央民族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12年。
陈安强、贡波扎西:《治疗社会恐慌的仪式——岷江上游“毒药猫”文化现象探秘》,《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年第3期。
(作者:浩然文史·神启)
- 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