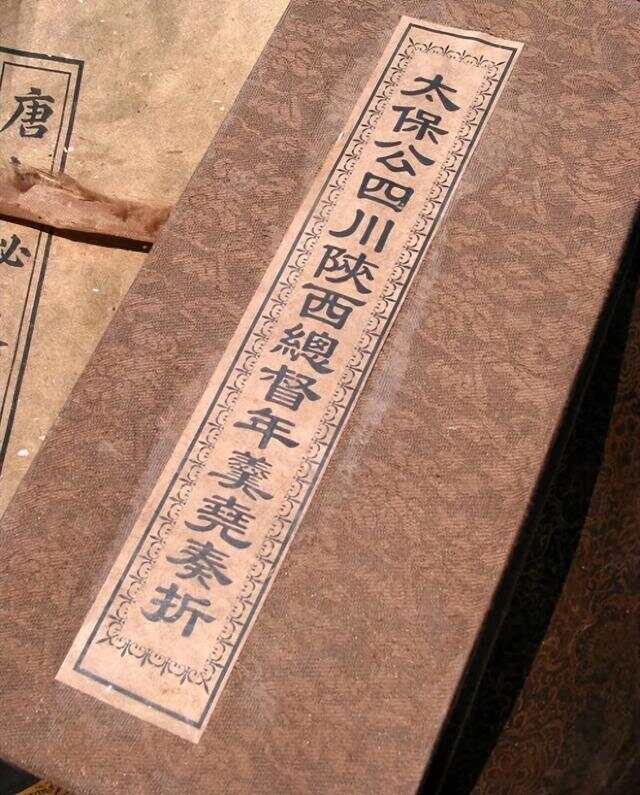新四军女院长收治国军伤员,伤好送行时,他忽然掏枪,打开了保险
1940年,新四军部队发生了一件怪事,野战医院的女院长栗秀真,她竟然让几位新四军伤员搬出去,腾病房给国军的伤员住。
三个多月后,院方为这些伤愈归队的国军士兵举行的送行宴会上,有一个国军的副官,却从怀里掏出一把手枪,打开了保险……
1915年12月16日,河南沁阳人崇义镇一个姓栗的老中医家里,传出一阵阵婴儿的哭声,这个婴儿就是栗秀真。
栗家祖传三代中医,栗大夫很想把自己的本事传给女儿,但是老祖宗的规矩是“传男不传女”,他为了难。思来想去,他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15岁那年,他把女儿送到河南汲县(今卫辉市)惠民医学专科学校学习西医。四年后的1934年,19岁的栗秀真毕业。她学习刻苦,成绩优异,毕业后被留在该校附属医院担任护士。不久后,她又担任了护士长。
1938年2月,日军占领汲县城,院长安排她到我党(董必武、陶铸)开创的湖北应城“汤池临时学校”任教。
1938年冬,鄂中地区燃起烽火,武汉、应城相继被日军占领。
1939年1月,在陶铸的领导下,“应城县抗日游击队”(简称“应抗”)成立,游击队军医院也随之成立,24岁的栗秀真被委以重任,当了院长。
让一个护士出身的女孩当院长,即使她再优秀,在今天看来都是不可思议的。但是在当时,这样做是出于无奈。
当时,“应抗”刚刚成立,成立的时候只有8条枪,后来陶铸又让人从香港买了20把德国造驳壳枪。万事开头难,游击队面临很多困难,新成立的医院缺医少药,医疗人才都到了大后方西南,栗秀真就成为“金疙瘩”,被委以重任再正常不过。
1939年6月,遵照中原局的指示,李先念、陈少敏来到京山养马畈一带高举抗日大旗,“应抗”被编入新四军,番号为“独立游击支队”。
木匠出身的湖北人李先念,在军事上很有一套,他21岁就任红三十军政治委员。白手起家的他,短短一年间,把人马扩充到一万。

1940年初,豫鄂挺进纵队宣告成立,原来的“应抗”医院,也随之升格为“新四军豫鄂挺进支队野战医院”。
栗秀真劳苦功高,自然还是院长。挺进支队是在夹缝里生存,每天跟日军打游击,野战医院的地址也不是固定的,搬家是常有的事。这不,1940年刚过完年,栗秀真的野战医院又接到上级的通知,搬家到湖北省京山县石板河畔的赵家冲一带。
得知消息,刚住进医院,做过手术的战士们一肚怨言,嘟嘟囔囔。可是当他们到了新驻地之后,当即眉开眼笑,因为京山山清水秀,丛林遍布,景色宜人,就像人间仙境,在这里养伤再合适不过了。

而且赵家冲紧挨着大山,地处偏僻,距县城有近百里路,相对来说也比较安全。
不光如此,挺进纵队宋(河)应(城)路西指挥部当时就驻扎在距此只有20里的八字门,即使发现敌情,肯定会得到预警,也不需要太担心。
可是,正当伤员们在这里安心养伤的时候,险情发生了。
1940年4月的一天,栗秀真正在忙着跟医护人员给一个伤兵做手术,一个新四军小战士跑了进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我是路西指挥部的通讯员,政委杨学诚让你们赶快转移!”

栗秀真听了不敢相信,这里如此偏僻,再安全不过,为什么要搬家。再说了,医院搬家可不像作战部队,起身就能走。医院里坛坛罐罐多,有医疗设备,医疗物资,手术床,搬家一次的难度可不小。
“医院附近出现了一支部队,还不清楚他们是哪一部分的,为防万一,上级命令你们迅速转移应城湖区去。”通讯员说。
栗秀真一听不再质疑,随即召开会议,安排转移。几个小时之后,准备完毕,这时候已经是日落西山,夜幕即将降临,正好借着夜色转移。
正在他们打算起身的时候,警卫战士前来报告,宋应公路出现很多军车,来历不明。

粟秀真不敢大意,就决定推迟转移,看情况再说。
次日下午,周围没有了动静,栗秀真与指挥部沈德纯主任指挥着队伍上路。可是刚走了不到十里路,又发生了意外。前面路口,出现一群军人,穿着跟八路军一样的军装,仅仅是肩章不同,他们是一支国军。
这伙人在前面设卡拦路,对来往的车辆进行检查。看到栗秀真他们到来,士兵把枪一横,拦住去路,喝道:“你们是哪部分的?”
栗秀真一听此人说的是广西话,不用说是桂军,心情便不再那么紧张,至少比遇到伪军要好。这样一想,她便上前答道:“我们是新四军,挺进纵队医院的。”
这时候从哨所中走出一个军官,瞪着眼睛说:“这种危险时候上哪去,你们也太胆大了吧?”

“不知道兄弟此话怎讲?”沈德纯主任开口说道。
“你们不知道吧,我们正在和日军交战,战场距离这里不到十里路,你们往前走不是送死吗?”军官不耐烦地说。
“可我们是医院,能待在半路吗?”栗秀真焦急地说。
“这……”军官犹豫了一下说,“这我也不能做主,等一下我请示一下上峰。”军官双手一摊。说完,那名军官将栗秀真他们带到位于孙家冲的国军指挥部。
到了门口,军官示意栗秀真他们停下,军官进去禀报。不一会,军官让沈德纯主任进去,却让栗秀真留在外屋。
在指挥部里,沈德纯见到一个40岁上下,身穿少将军服的国军高官。此人身材魁梧、高鼻阔口,四方脸上一只鹰眼咄咄逼人。
之所以说是一只,因为此人是个独眼。此人虽然长得霸气,但是很谦逊,他主动走上前,跟沈德纯握手,然后自我介绍道:“卑职乃第94军(驻地广西柳州,士兵大多是广西人)副军长牟廷芳,奉上峰命令攻打驻扎在应城的日军,你们是哪一部分的?”
沈德纯主任微笑着说:“我们是新四军挺进纵队……”

一听到“新四军”三个字,牟廷芳脸色大变,眉头紧锁,脸上肌肉抽搐,双手也不自觉地攥成拳头,额头青筋突起。沈德纯一看心说不好,此人肯定跟新四军有过节。
还没等牟廷芳开口,一枚炮弹呼啸而来,在附近爆炸。虽然距离还有百米远,但是也让脚下的大地颤动,真震得人耳朵嗡嗡直响。
炮声一响,说话都听不见了,大家不再说话,坐到凳子上等待。炮声响了十几分钟之后停止了,接着是机关枪的声音——战斗打响了。

炮响的时候,栗秀真已经被叫到了指挥所,见枪声响起,她走到牟廷芳跟前大声说:“将军,开战之后,肯定出现很多伤员,要不要我们救治伤员?”
牟廷芳眼一瞪,说:“看你说的,仗还正式开打,你就咒我的士兵受伤?”
栗秀真并不介意他的态度,而是和颜悦色地说:“将军,要打仗就会有伤员,我们的士兵又不是红枪会、义和团。”
见栗秀真说话不紧不慢,牟廷芳反而显得有点尴尬,但仍旧梗着脖子说:“谢谢这位女士的好意,我的伤员不会扔到阵地,我会安排,你们就甭操心了。”
这时候,他的副官走了过来,伏在他耳边悄声说:“军座,我们打了多日的仗,药品已经告急,能不能让新四军卖给我们一些药品?”
副官的话声音不大,但还是让沈德纯听见。没等牟廷芳说话,他便抢先说道:“我军的药品也库存不多,但可以先给贵军一些,但我们不会卖,都是中国人,都是打鬼子,收钱就见外了。”
牟廷芳一听,眼睛瞪得老大,显然这话出乎他的意料。他不再高傲,而是感激地说:“那太好了。”
说话间,总攻开始,战况激烈,伤员也陆陆续续被救护队抬到了到指挥部不远的一所学校。就在这时候,指挥所里屋的电话响了,牟廷芳对栗秀真他们抱歉笑了笑,到里屋去接。
放下电话,牟廷芳走了出来,对沈德纯和栗秀真说了一句话,让二人意想不到:“二位,牟某想拜托你们一件事。”
这话让二人感到惊讶,刚才还端着架子、盛气凌人的少将,为何转眼间态度大变,判若两人?
原来,牟廷芳刚接的电话是上峰打来的,要他立刻率部转移。这一来,伤员便成了问题,根本就无法带走。

“部队转移,伤员不能带,但是牟实在不忍心撇下他们,弟兄们跟着我南征北战,是为国受的伤啊。”牟廷芳声音低沉地说,“贵军可不可以先帮忙照看一下?”
闻听此言,沈德纯和栗秀真都没有开口。伤员看样子有二三百人,新四军医院一旦接下这批伤员,那就要给他们处理伤口,做手术。一旦这样,医院还如何转移?
桂军转移之后,日军到这一带来是板上钉钉的事,新四军的伤员和医护人员处境就会非常危险。
这样一想,二人犹豫起来,许久没有开口回应。看到二人为难的表情,牟廷芳长叹一声说:“二位莫为难,伤员只好丢在这里,生死有命吧。”
听了这话,栗秀真眼眶湿润,这些伤员都是抗日健儿,丢在这里不管于心不忍。
这样想着,栗秀真给沈德纯使了个眼色,二人到外面商量了一下,做出了艰难的决定:接收这批伤员。

听了他们的决定,牟廷芳再次被感动了,他紧紧握住二人的手声音微微颤抖着说:“卑职谢谢你们了,日后,牟某一定要把你们的义举向委员长汇报!”
牟廷芳说着,又指着自己失明的那只眼睛说:“实话告诉二位,之前我跟贵军有深仇大恨,所以才下令拦截你们。”
牟廷芳是贵州朗岱(今六枝市)人,1904年出生,黄埔一期生,他不但深受蒋校长欣赏,也是总教官何应钦的得意门生。
在何应钦的安排下,他在1928年还到日本学习军事,让别的同学妒忌,能有这样机会的人,即使是黄埔生也是千里挑一。
回来后,牟廷芳就开始死心塌地为蒋家王朝卖命,进攻苏区,以报答蒋校长与何老师的“知遇之恩”。

因为屡立战功,在1936年,牟廷芳被委任为贵州省保安处副处长。上任不久,便迎来一场恶战,对手是贺龙、任弼时率领的红2、6军团。战斗中,牟廷芳冲锋在前,被子弹击中右眼。从此,牟廷芳对红军恨之入骨,发誓要报仇。
可是当年4月,红军就西去离开贵州,牟廷芳虽然不甘心也只能作罢。
转眼间,时间来到1940年,时局发生了很大变化,昔日战场的敌人红军和白军,在国恨家仇面前已经成为友军。但牟廷芳小肚鸡肠,仍然耿耿于怀,不忘报仇。因此,当他听说新四军要从自己的地盘经过的时候,就想报仇。
当时国共两党正在合作抗日,他再怎么也不敢真正出手,只能借机刁难一下。没想到,新四军如此顾全大局,高风亮节,让他很是愧疚,感到无地自容,对我军的态度也迅速转变。
解放战争期间,牟廷芳深受蒋介石赏识,担任天津警备司令部司令官,但是对内战态度消极,没有主动进攻解放军,以至于被蒋介石撤职,1953年在香港病逝,此乃后话。
这批留下的蒋军伤员人数确实不少,有300多人,这给本来就人力物力资源短缺的新四军医院带来很大压力。在此情况下,栗秀真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让正在住院的新四军伤势较轻,或者已经快要康复的伤员提前出院,住在老乡家。
情况紧急,来不及请示上级,栗秀真自己做主,承受巨大压力。不过事后请示上级之后,上面并没有责怪她。
栗秀真带着医务人员度过了多少个紧张的白天,度过了无数个不眠之夜。在他们的精心照料下,94军的大多数伤兵很快康复。

以前受牟副军长的影响,很多蒋军官兵对新四军充满敌意,没少跟新四军搞摩擦,如今见新四军医院的天使们以德报怨,哪怕是铁石心肠也被感动。
临走之前,有的士兵来到院长办公室说:“栗院长,我们想参加新四军。”
栗秀真听了连忙笑着解释说:“我们现在都在国民政府领导下,你们如果参加新四军,我党没法给重庆交代。”
经过一番劝说,栗秀真才让那些士兵依依不舍离开。
也并非所有伤员都感激新四军,也有一部分人中毒太深,对新四军看法不变,说我军救治他们是有目的,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
“新四军为啥对我们这么好?他们就是想策反咱们,谁要是不同意的话,到时候都会被活埋。”伤兵中,一个姓吴的副官说。
1940年7月下旬,是桂军伤员归队的日子,栗秀真设宴为他们送行。聚餐时,发生了意外。酒过三巡之后,有个副官突然掏出一把手枪,打开保险。
在场的人目睹之后,全都看震惊不已:这小子要干什么?幸好,一旁有个国军士兵反应敏捷,瞬间将其控制,把枪夺下,危机得以解除。
副官为什么这样做?
审讯他的时候,他说:“我听到有人说,新四军要设鸿门宴,在宴会上将我们解决。所以我就偷偷带了一把手枪,打算万一到时候,跟你们新四军拼个你死我活。”
栗秀真听了哭笑不得:“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自己常干坏事,认为别人也像自己一样卑鄙、龌龊。”

那位副官这才知道自己上当,误解了新四军,但是他仍旧忐忑不安,认为新四军饶不了他。结果出人意料,他不但没有被惩罚,手枪也物归原主。
他激动地说:“我这辈子啊,都不会再向新四军开一枪!”
常言道,一时胜负在于力,千秋胜负在于理;靠暴力只能取得一时的胜利,真正笑到最后的,是跟正义站在一起的人。
新中国成立后,栗秀真先后担任湖北省卫生厅厅长、卫生部防疫司副司长。
来源:《栗秀真文集》中国人口出版社1995-12
- 0000
- 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