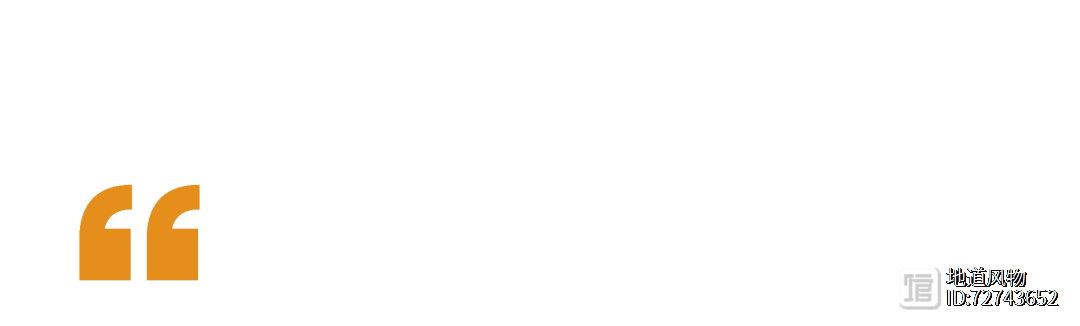洪涛:文学地理学、归因谬误与南北方文学(读张隆溪教授的英文版中国文学史・三)

近人柳存仁(1917—2009年)在《上古秦汉文学史》中谈及文学史的书写,他说:“对于产生某一时期文学之时代精神、社会环境、文化氛围,亦应有确切之认识,再依据事实认识而考察其所发生之影响。”(商务版,1948年,页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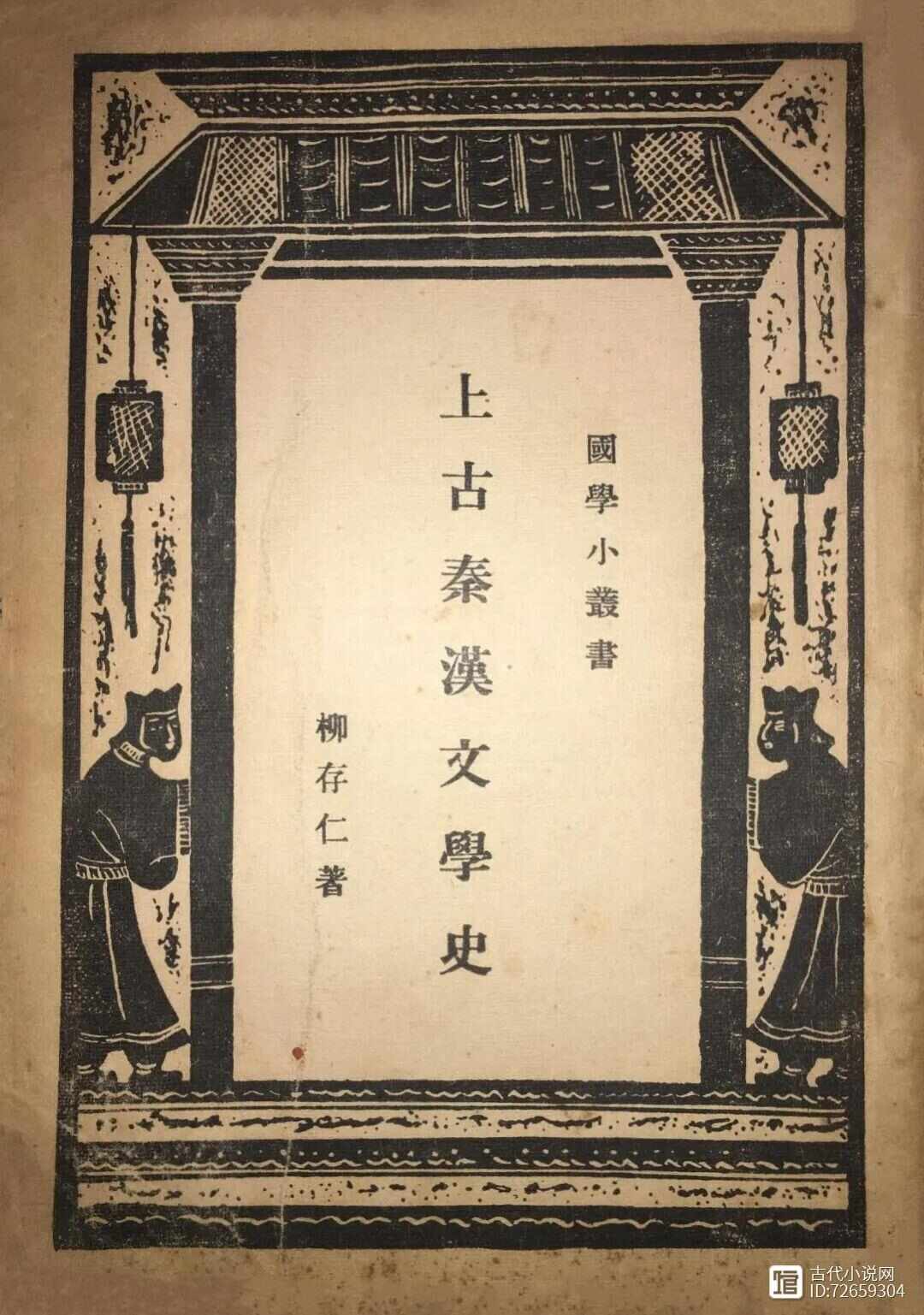
柳存仁《上古秦汉文学史》
张隆溪教授撰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Routledge, 2023),内容也体现柳存仁的书写主张 (环境影响论),例如,我们看到张教授论及地域气候差异对文学的影响,他说:Living in different climates, people tend to establish different lifestyles; the northern style in general is more practical and austere, while that of the southerners more imaginative and luxurious.(p.27) 大意是:北方作品一般而言务实而简朴,南方作品中多想象之词,比较绚丽繁缛。
十九世纪末,日本早期的中国文学史著述在丹纳(Hippolyte A. Taine)“环境论”的影响下,提出过“南北文学观”。日本学者这样区分南北文学特征,对中国的早期文学史编纂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具体论证地域影响作品特征的时候,张教授的说法启人疑窦,例如,他说:In ancient times, however, geographical and climatic differences did have a bigger influence and they clearly manifested themselves in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ancient anthologies. Poems in the Book of Poetry, as we mentioned earlier, have mostly four-character lines, that is, lines of four monosyllabic words, …。(p.27) 张教授认为古时地域和气候的影响较大,并以先秦诗集为例说明作品的特别风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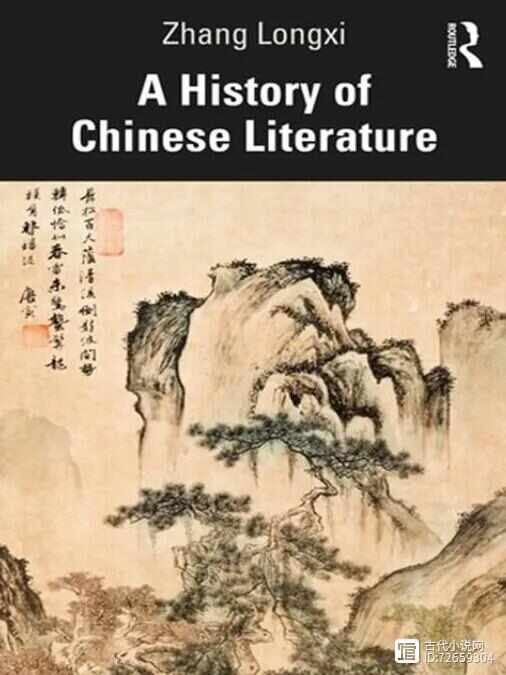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笔者认为,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2023年)书中建立的因果关系,值得再三斟酌。

北方的地理、气候影响了《诗经》的特征?
也许因为《诗经》之中以四言诗行居多,所以,在张教授眼中,四言(相对于五言、七言)显得比较austere(简朴),是北方文学的特点之一。
然而,在笔者眼中,用诗行的字数较少来“印证”地理和气候的影响,未必妥当。为什么?建安时期三曹父子的例子可以说明笔者的看法。
现存曹操的诗篇多为乐府歌辞,他尤其擅长四言和五言。至于曹操的儿子曹丕、曹植也和曹操一样长时间处于北方,曹丕、曹植的五言诗各占他们现存诗篇的一半以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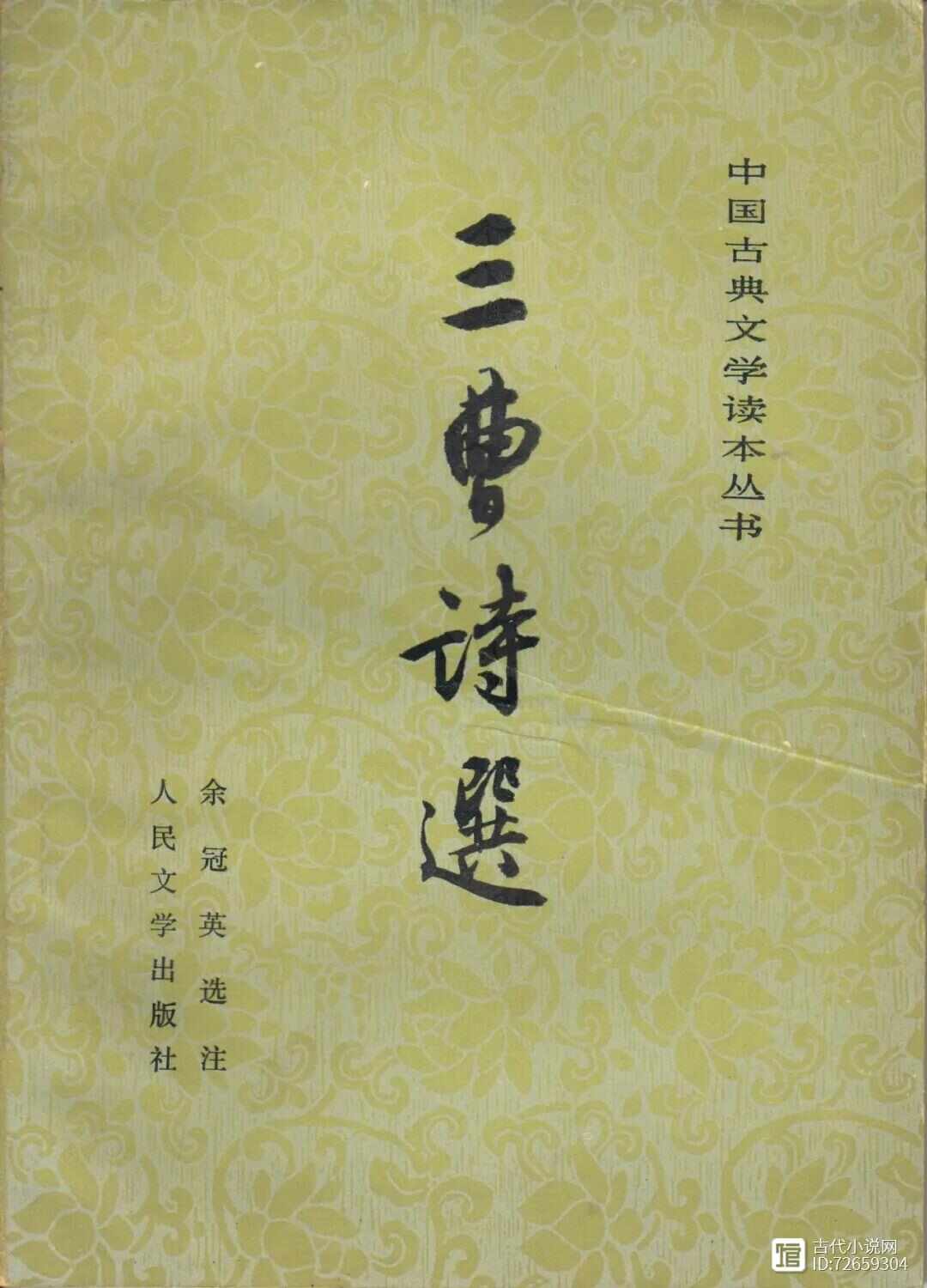
《三曹诗选》
曹丕《燕歌行》据说是中国诗歌史上第一首完整的七言诗。曹植现存四十多篇赋。三曹的情况(诗行长短)不一致,这现象正好说明地理和气候对诗行的长短没有必然的影响。到了南北朝,北方诗人也甚少写四言诗。
如果说,只谈三曹的诗篇,取样(sampling)不够多,那么,何妨连“建安七子”一并考虑?
“建安七子”是孔融、陈琳、阮瑀、徐干、王粲、应玚、刘桢。他们大多数在北方活动。据说,孔、徐、王、刘是山东人,应、阮是河南人。陈琳投靠河北袁绍,后来加入曹营。他们皆曾居邺城(今河北临漳),亦称“邺中七子”,七子的诗篇,却是罕见四言句(郁贤皓、张采民《建安七子诗笺注》巴蜀书社,1990年,页16)。刘勰评七子,说他们的诗篇“梗概而多气”。这评语也不适用于《诗经》。
张教授又说The Book of Poetry has a rich variety of themes and scenes, but by and large, these are represented in a realistic manner.(p.27) 所谓a realistic manner,应该是指“诗风贴近现实”,可是,笔者已经在别的文章中论述过:《诗经》的篇章中也涉及神话故事、神鸟、神兽。除非能证实那些故事和鸟兽是现实世界存在过,否则,realistic这标签未必适用于涉及神话神迹的诗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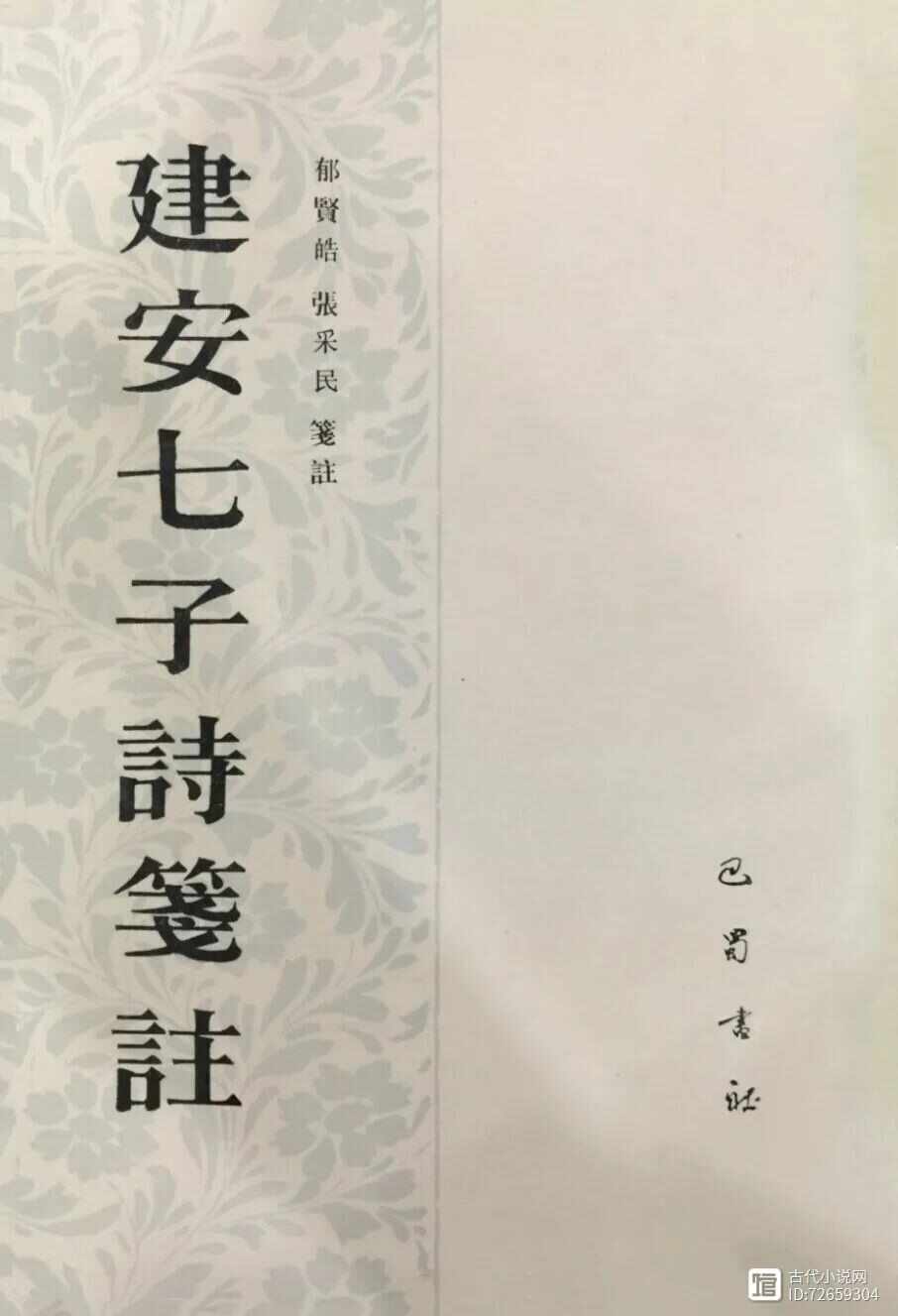
《建安七子诗笺注》

《诗经》之中,没有南方诗篇吗?
《诗经》之中,也有些诗篇写南方的长江、汉水,例如:《大雅・江汉》写“江汉浮浮,武夫滔滔”,又例如,《召南・江有汜》写“江有汜,之子归,不我以。”《卫风・汉广》写“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江”就是长江;“汉”,就是汉水。换言之,《诗经》不单只收录北方诗篇。
何为南方?何为北方?分界线在哪里?
1908年,地理学家张相文 (1867—1933) 提出以“秦岭—淮河线”(秦淮线)作为中国南北分界线(张相文《新撰地文学》上海文明书局,1908年)。秦岭是中国中部东西延伸的山脉,横跨甘肃南部、陕西、河南,长约1600公里。淮河长约1000公里,由西至东,流经河南、安徽、江苏三省。秦淮线除了在地理上是处于地域正中,也考虑气候、降雨降雪、温度、农业、植物等分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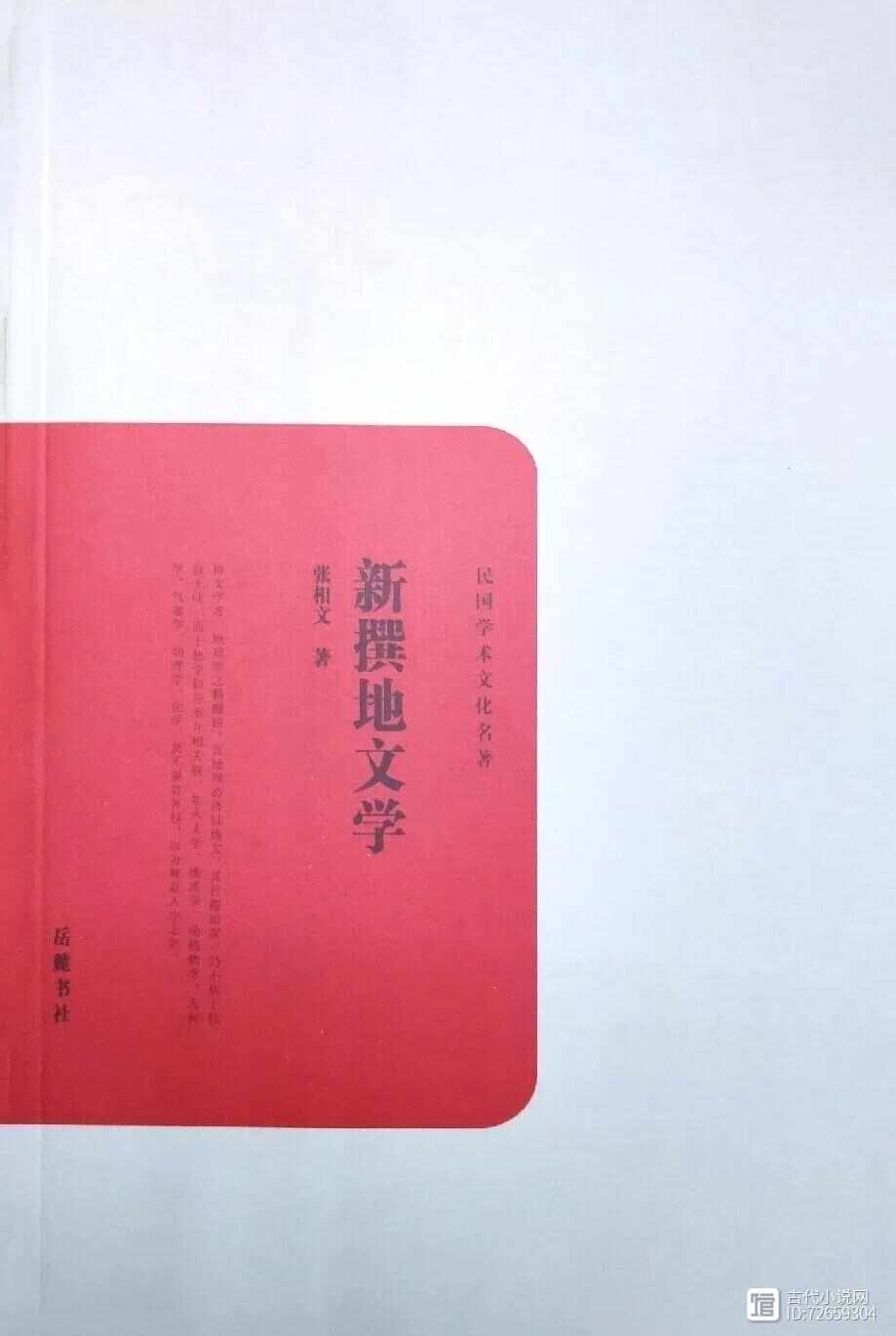
《新撰地文学》
无论如何,长江流域往往被视为南方,这点在小说《三国演义》赤壁之战中体现得很清楚。

《楚辞》中的四言句式与归因谬误
张隆溪教授论及南方地域气候对《楚辞》的影响,他说:works in the Songs of Chu have a greater variety of lengths, from five to six or seven characters, often with an additional character as an exclamatory particle. 这句话中,the Songs of Chu就是《楚辞》。
上述言论,值得商榷。不错,《楚辞》之中,是有六言句、七言句,然而,from five 改成from four会比较好,因为《楚辞》中,《天问》一篇的开端就是一连串的四言诗行:“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暗,谁能极之?冯翼惟象,何以识之?明明暗暗,惟时何为?阴阳三合,何本何化?圜则九重,孰营度之?惟兹何功,孰初作之?斡维焉系,天极焉加?八柱何当,东南何亏?九天之际,安放安属?隅隈多有,谁知其数?……”

洪涛《从窈窕到苗条:汉学巨擘与诗经楚辞的变译》
《天问》之中有这么多四言句,又不是属于少数,何以南方人的四言句就不入张教授之眼?除非《天问》不属于 the Songs of Chu, 否则,from five to… 之说宜修改。
《天问》之外,《九章・橘颂》开头:“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又,《九章・招魂》:“魂兮归来!西方之害,流沙千里些。”明显也有四言句子,岂能忽视?
至于张教授说《楚辞》句中常有an additional character as an exclamatory particle,应该是指“兮”等语气词的使用。张教授没有说错,“兮”字常见于《楚辞》。
不过,《诗经》实际上也使用“兮”字句式,而且在不少诗篇中出现:
见于句中者,例如《周南・葛覃》“葛之覃兮,施于中谷。”见于句尾者,例如《召南・摽有梅》“摽有梅,其实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句中句尾皆用者,例如《邶风・绿衣》“绿兮丝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无訧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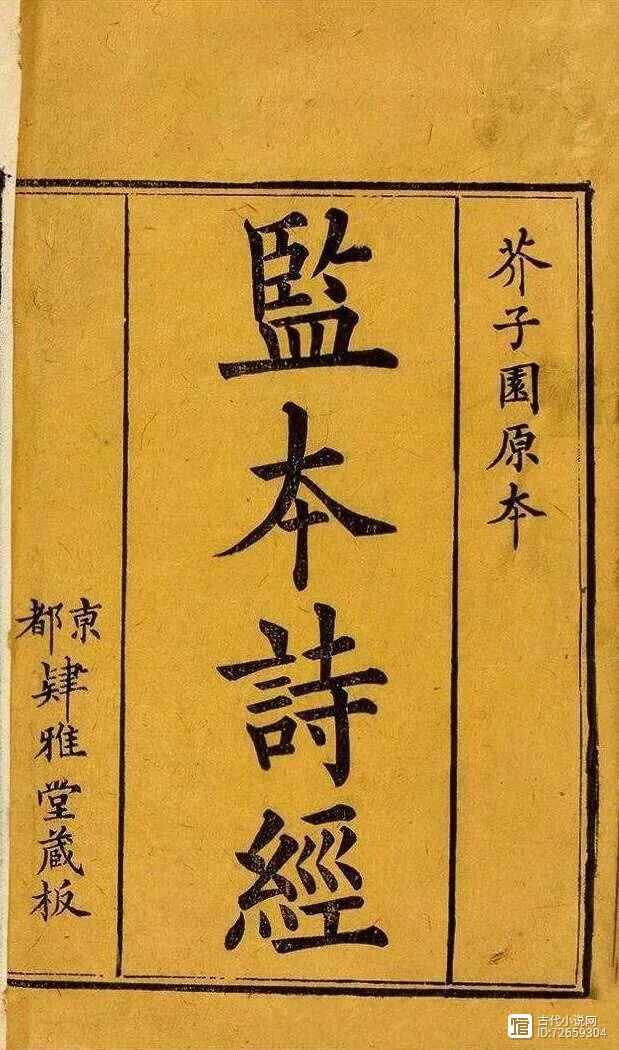
清肆雅堂刊本《诗经》
通篇句句用“兮”者,例如《魏风・十亩之间》:
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
行与子还兮。
十亩之外兮,桑者泄泄兮。
行与子逝兮。
同类例子还有《陈风・月出》“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纠兮,劳心悄兮!月出皓兮,佼人懰兮,舒忧受兮,劳心慅兮!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夭绍兮,劳心惨兮!”《桧风・素冠》,也是全诗句句有“兮”字。
因此,以诗句每行字数和叹词的使用来说明不同地域对作品的影响,在归因方面(attribution) 恐怕是有问题的,例如,《天问》《橘颂》四言句的成因是什么?《天问》《橘颂》难道也受北方地理和气候影响?又,曹丕身处北方,何以他创出七言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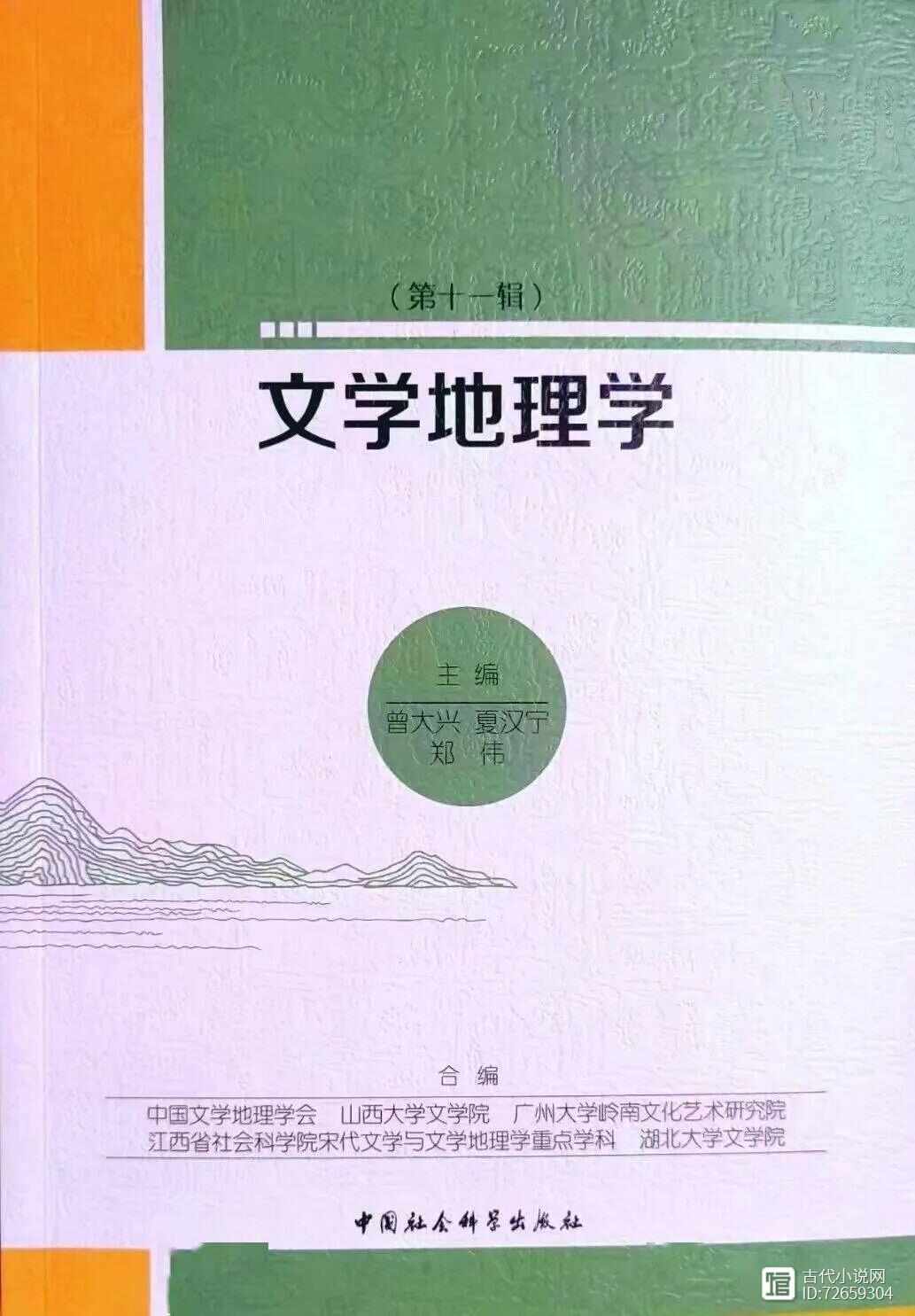
曾大兴、夏汉宁主编《文学地理学》
与其将《楚辞》的句法特征归因于地理气候,不如考虑:南方诗人参考过《诗经》。一般史家强调诗、骚不同,读者没有预期诗、骚句式实有雷同之处(unexpected affinities)。如果是为了论述的方便而刻意将一部分文学特征抑压掩盖,恐非史家所应为。

文学史话语,会过度概括吗?
在讨论南北朝时代的文学时,南北差异的话语(north-south differences)又再出现:Because of the differences in climate and customs, i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the south and the north acquired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which manifested in literary creations with quite different styles. (p.71) 不过,这回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2023年)除了气候影响文学外,还增说风俗、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等因素影响文学。
由于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书中没有详细论述以上各项的情况,譬如南北经济状况怎样具体影响文学作品的风貌,笔者无法进一步复按。

《中国中古文学史 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
民国时期,刘师培(1884—1919)在《南北文学不同论》一文中说:“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际,多尚虚无。”请注意:他用了“大抵”“多尚……”来减低过度概括(over-generalization)之虞。
关于 fallacies of generalizations (概括谬误) 这方面,读者诸君可以参看David H. Fischer, Historians' Fallacies: toward a Logic of Historical Thought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1970), pp.103-4。这书专论“史家的谬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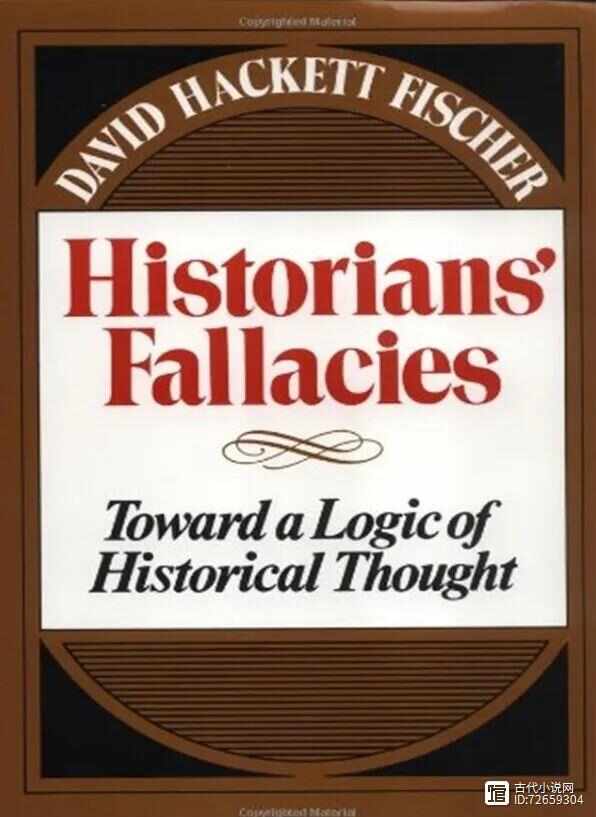
《史家的谬误》英文版
上世纪中后半叶,内陆出版的文学史书多以屈原作品为“浪漫”或“浪漫主义”的代表作,例如: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页70-72竟然五次用“浪漫”来形容楚辞﹔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一段之中,六用“浪漫主义”。
不过,一般学者解读《楚辞》作品还是离不开楚国政局的现实,就连降神之作《九歌》也被解读成屈原思念现实世界中的楚王。
由于诠释《楚辞》往往倚重楚国的国运(楚国的“现实”),后来屈原“爱(楚)国主义”成为文学史书写中的重要话语,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就是好例子,读者可以参看该书第五章第三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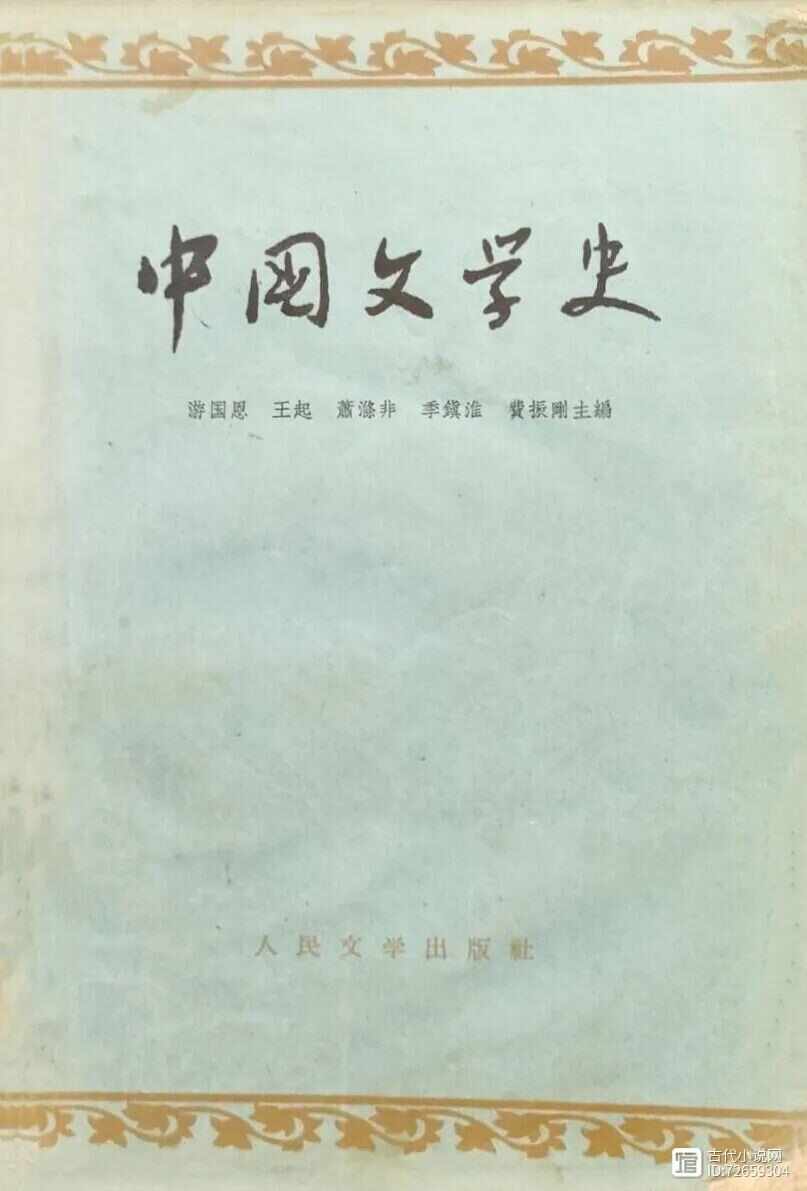
《中国文学史》,游国恩等人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
到了二十一世纪,北京大学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仍然保留“(屈原)爱国”的论述,但似乎刻意回避沿用“主义”二字。
“爱国”自是宝贵,于是,《楚辞》中纵有鬼神巫觋也都不成问题了, 言论也罕见于近五十年的文学史书。《楚辞》得到评价比《诗经》还高。
- 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