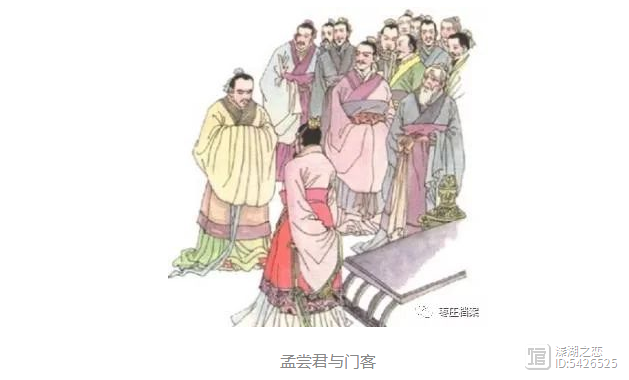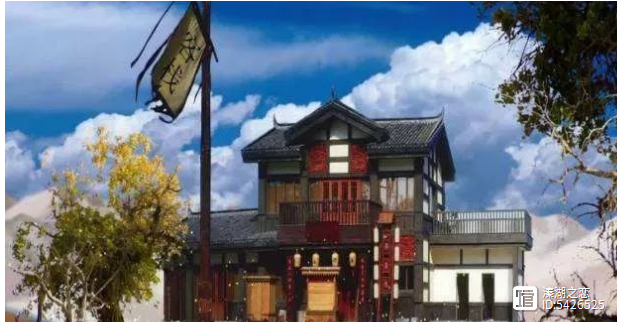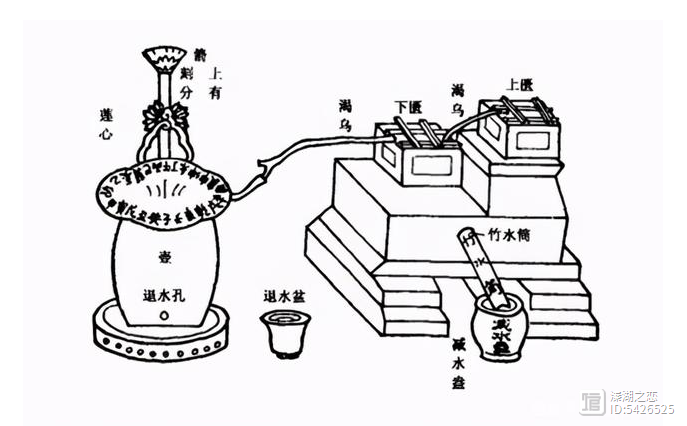长安城,请铭记他的回眸
终唐一代,长安始终是唐人无法回避的字眼,谈长安或轻或重谈到唐人,谈唐人又或多或少提到长安,人与城就这样相辅相成联系在了一起。作为承载着说不尽厚重历史和数不清权柄宝盖的都城,许多被史书镌刻姓名的人都留下了自己对这座城市的感悟和怀想。
长安在李白笔下,是一片月色下万户捣衣的真情实意,在王维心中则是九天阊阖和万国衣冠的壮阔盛景,等到了老杜所见,国破惊心的悲痛刺激着每一个人的神经。

清 唐岱 院本新丰图局部
卢照邻与他们都不同。这个出身望族却仕途坎坷的才子自然不会知道未来的悲欢,但他笔下却好像生出了缕缕无形的丝线,把他的长安与后辈的长安串联在一起,叫人读了遍体生寒。
彼时卢照邻已经不再是当初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慷慨激昂的言辞和略显幼稚的奇思早就成为了过去式,可长安的风貌却让他恍惚觉得好像什么都没有改变。无论何时,长安的街道依然四通八达,贵人们描龙绣凤的车盖随着车子的前进而微微晃动,幅度惊扰了垂下的流苏,引来对面拉车的高大骏马的好奇,连蹄声都变小了几分。

明 仇英 清明上河图局部
卢照邻心想,在寸土寸金的长安城,连风都是带着富贵奢靡气息的,熏得人睁不开眼。可他又止不住觉得心酸,年少时他曾不止一次幻想过自己也能坐在这样的车里出入于长安城每个王公贵族的府邸,前后奴仆环绕,左右奉承不绝,甘愿在这暖风的吹拂下沉沉睡去。
若是寒门白丁常有这样的幻想,旁人十有八九会笑他痴人说梦。但卢照邻不同,他出身簪缨世族范阳卢氏,作为名列“五姓七族”的高门子弟,卢照邻拥有常人难以企及的家学渊源,有唐一代门第观念依然强烈,世家门阀有着近乎垄断的人脉和资源。
卢照邻少时就跟随当时的大家曹宪和王义方学习,深得其真传。本就聪慧的少年在名儒身边耳濡目染,自身的学问更是日日精进。那时是算是他最骄傲快乐的时候,占尽天时地利人和,放眼望去前方是一片坦途。

南宋 刘松年(传)山馆读书图
一群鸟的叽喳声在此时不合时宜地响起,它们绕着颜色鲜艳的花朵久久不愿散去。不远处的树上缠绕着一眼难以估出长度的虫丝,长安的蜂蝶也带着一股豪气,成群结队地飞过,只留下被斑斓色彩晃了眼睛的人还在原地不知所措。蝶群飞过森严气派的宫墙,雕刻合欢花的窗棂和金凤装饰的房脊是它们暂歇的地方,歇够了就继续在雕梁画栋间穿梭,常人一辈子可能也看不到一次的场景对它们而言已是司空见惯。
犹记最初入仕时,卢照邻曾在长安短暂结识过一些歌姬舞女,额点花黄姿容曼妙的她们和着歌翩翩起舞,妖娆的背影不知晃晕了多少眼睛。他那时最常听一些靡靡乐曲,曲调内涵离不开儿女情长,听得久了,他也来了灵感,一句“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羡仙。”足够世间痴男怨女在进行爱情誓约时流下的泪水汇成河东流不返。
此时在文坛初露锋芒的卢照邻在来济的大力举荐下成功与邓王结识,后者也成为了他人生中最大的贵人。
邓王李元裕乃是高祖皇十七子,为人风雅,善谈名理,也许是为了保全自身,也许是真的淡泊名利,这位王爷算是安分守己。得到邓王赏识的卢照邻更是如鱼得水,入职邓王府担任典签一职。
想来卢照邻与邓王之间的感情真的可以称一句“情如鱼水”,前者阅遍王府海量藏书,甘愿做着没有实权的文书工作,后者则盛赞对方是“此吾之相如也”,将卢照邻比喻为汉赋大家司马相如,这段知遇之恩也传为佳话。
在王府的这段日子大概是卢照邻一生最闲适的好时光,随着邓王离世,卢照邻也离开了王府,调任益州新都尉,开启了他后半段直线下降的人生。

北宋 郭熙 (传) 行旅图页局部
在偏远的益州,卢照邻开始感觉到忧虑,旁人都在忙着建功立业,只有他停滞不前,除了被风霜侵染的脸庞之外似乎什么都没有获得。那段时间,除了频繁和好友唱和外,他更多地想起长安。
他想起长安的夜晚,娼家门庭永远灯火阑珊,歌不断,舞不停。无论是身骑白马的五陵少年,还是白日策划着刺杀公卿的提剑刺客,或者禁军的官吏都汇集在此忙着享乐,贪欢淫靡的气息弥漫不绝,再想起鸟雀欲栖的廷尉门前,卢照邻只隐隐觉得不安。
这份不安在卢照邻心里逐渐蔓延,朝中势力如同藤蔓一样错杂交互,文臣武将更是斗得不亦乐乎,每个人都在瞬息万变的世事里苦苦挣扎,你方唱罢我登场,名叫长安的戏台上每日都上演着精彩残酷的戏码,连他这个边缘人物都能感知一二。
之后,在蜀中蹉跎数年的卢照邻终于结束漫游,背上行囊返回洛阳。神都的繁华短暂抚平了他的悲伤,可在洛阳的平静时光没有持续多久,他就迎来了牢狱之灾。

明 佚名 停舟访梅图
都说才华是双刃剑,有时候会助人青云直上,有时候则会成为刺向自己的利器。关于卢照邻这场牢狱之灾,流传最广的说法是他所作《长安古意》中“梁家画阁中天起,汉帝金茎云外直”之句惹恼了武三思,被他一怒之下下了大狱。
在狱中的卢照邻坚定了自己的想法,诗为情生,写诗抒情有何错?他并不恼,只是更加觉得造化弄人,想他一个世家子弟,做着低品小官,拿着微薄薪俸,蹉跎半生归来,千言万语都汇成一句世事无常。
这样来看,在《长安古意》中,结尾四句算是当时卢照邻内心深处最羡慕也最令他安心的美好期盼,昔日歌舞场今日连天衰草,今日田舍汉明日官拜朝堂。参透枯荣轮转的真理才更加羡慕扬雄,守着寂寂寥寥的扬子居,著着年年岁岁的一床书,不被外物影响。
寂寂寥寥扬子居,年年岁岁一床书。
独有南山桂花发,飞来飞去袭人裾。
——卢照邻《长安古意》后四句
卢照邻以南山桂花为全诗画上了句号。前面所有的豪门富贵和美人如画最终都只止于飞舞零落的花瓣,他把自己的感悟提笔写下,以一个旁观者的姿态,想要告诉所有人长安城光鲜外表下的暗流涌动。虽不脱六朝余韵,但其中讽喻手笔已胜过空泛奢靡的宫体太多,以至于闻一多先生有如此评价:“他是宫体诗中一个破天荒的大转变。一手挽住衰老了的颓废,教给他如何回到健全的欲望;一手又指给他欲望的幻灭。”
一首《长安古意》,使卢照邻诗名更盛,更奠定了四杰文章“不废江河万古流”的磅礴基础。
经友人救助出狱的卢照邻没有获得他期盼中的闲适生活,此时他已然身患风疾缠绵病榻,而后竟然发展到手足残废的地步,这对于本性骄傲的他而言是毁灭性的打击,身体的病痛无时无刻不折磨着他的心灵。虽有药王孙思邈和一众友人不辞劳苦地救护,卢照邻病情仍是愈加恶化。
新唐书载:“照邻自以当高宗时尚吏,己独儒;武后尚法,己独黄老;后封嵩山,屡聘贤士,己已废。”读完只感悲戚,无数阴差阳错构筑了卢照邻,他有传世的才笔,却无腾达的运道,令命途坎坷四字都不能完全概括他的一生。
也许是为了保全自己仅剩的尊严,也许对这个世界不再存有留恋,四十岁的卢照邻最终选择与亲属诀别,拖着病体以决绝的姿态投水而亡。
一番涟漪后,只余南山盛开的桂花乘风飞到长安,落在人们的衣裙上观看四周川流不息的车马,高官显贵的门庭和盛装丽人的容颜,此后花瓣照样西去,颍水依旧东流。
作者:苍鸾
本文为菊斋原创首发。公号转载请联系我们开白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