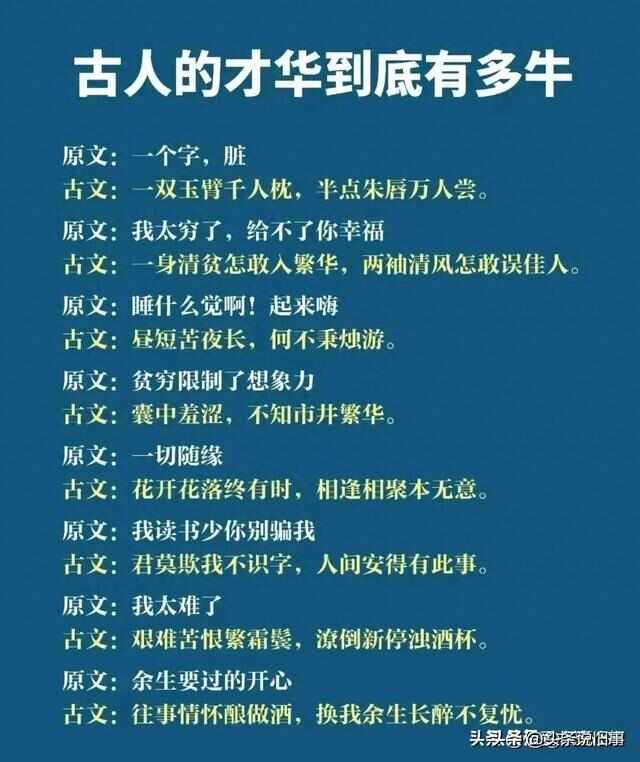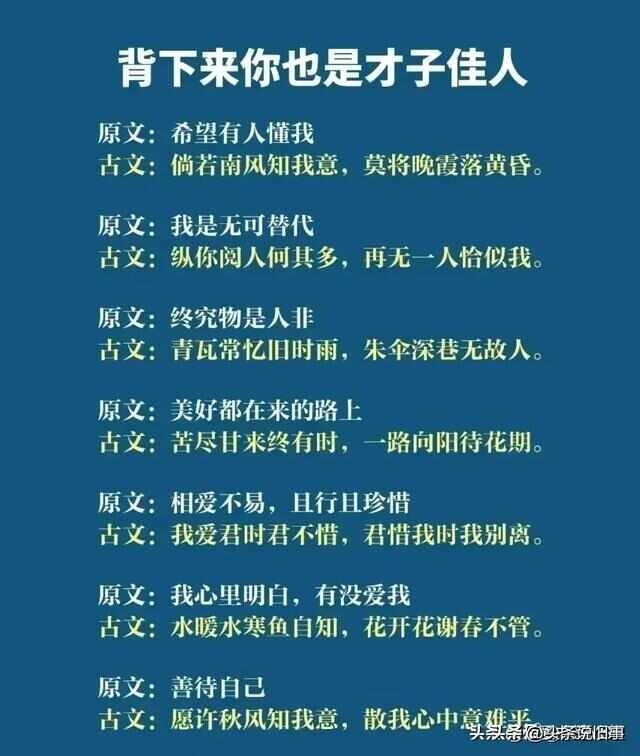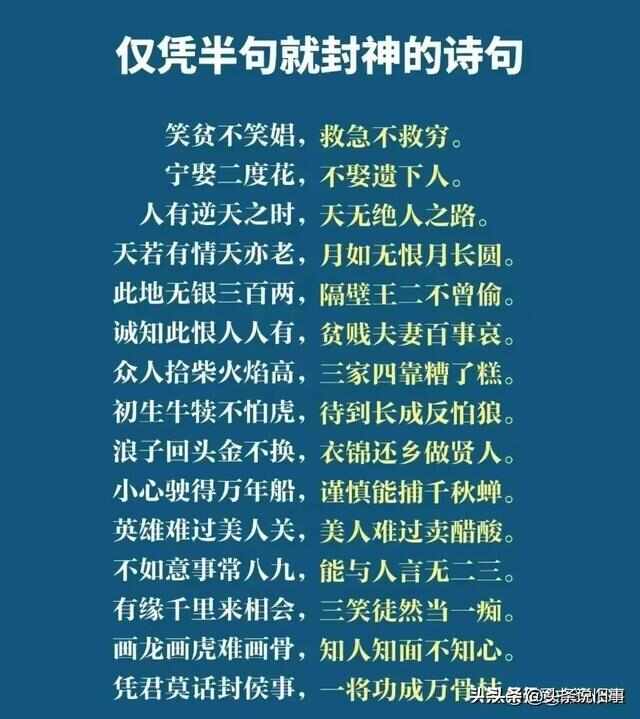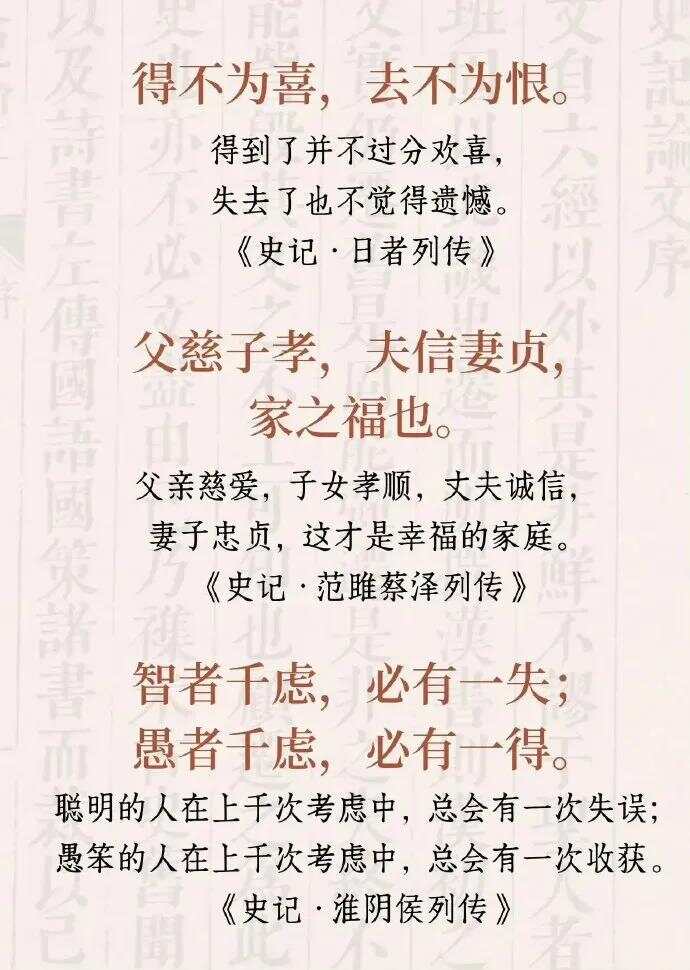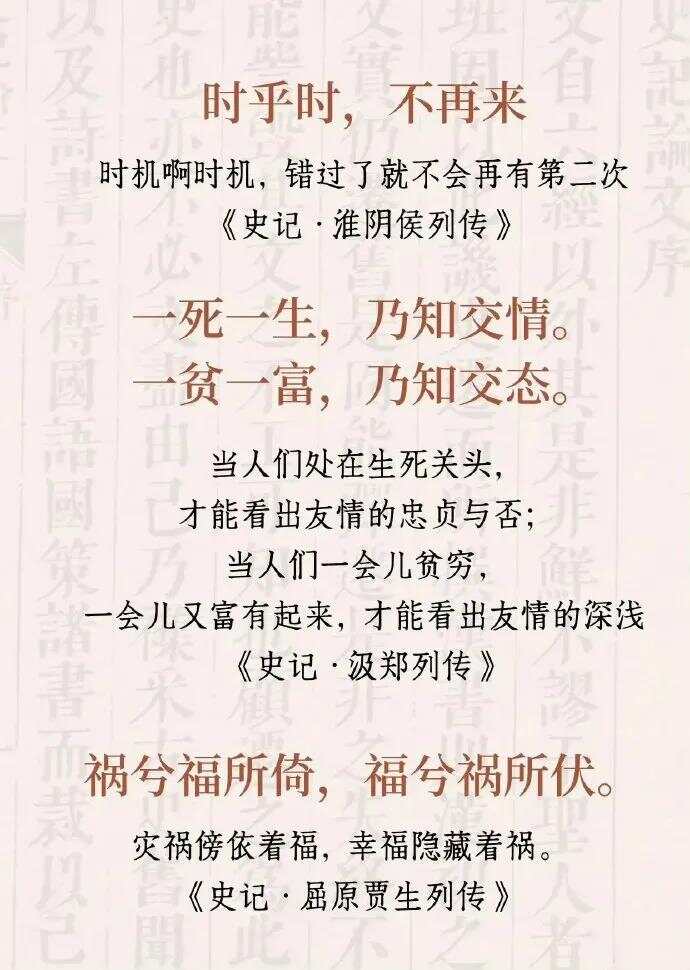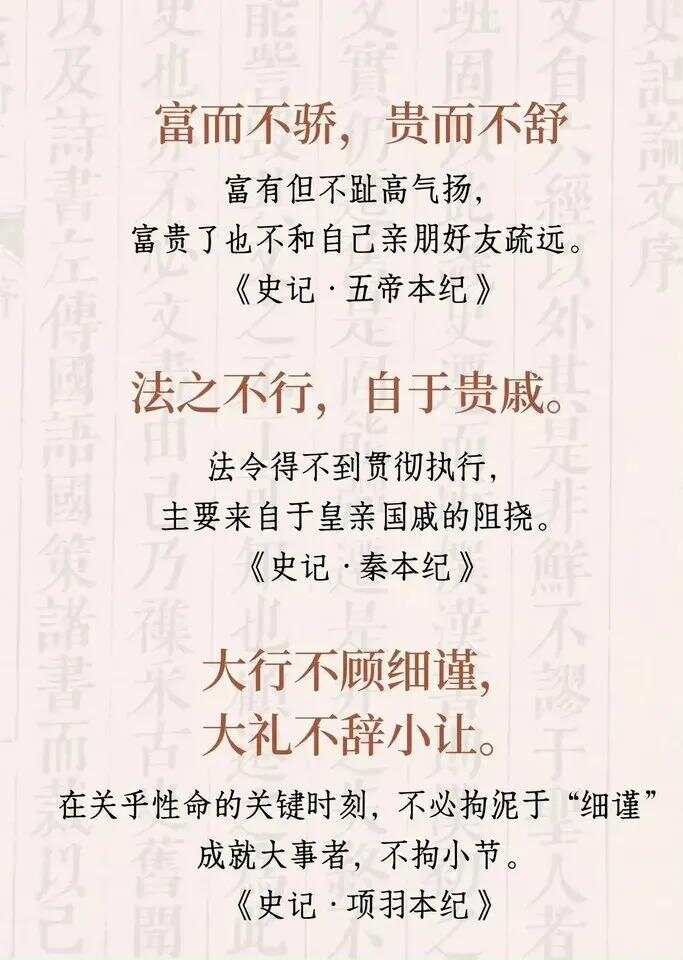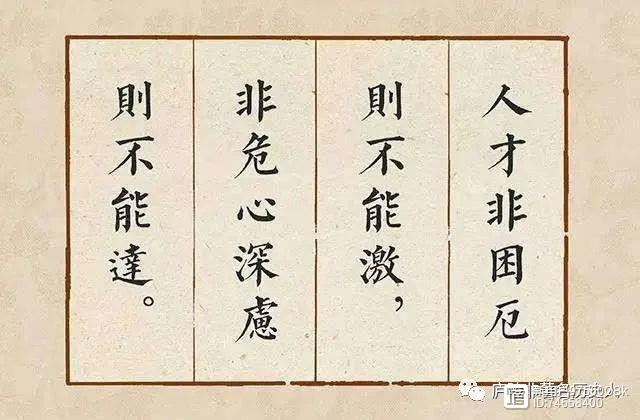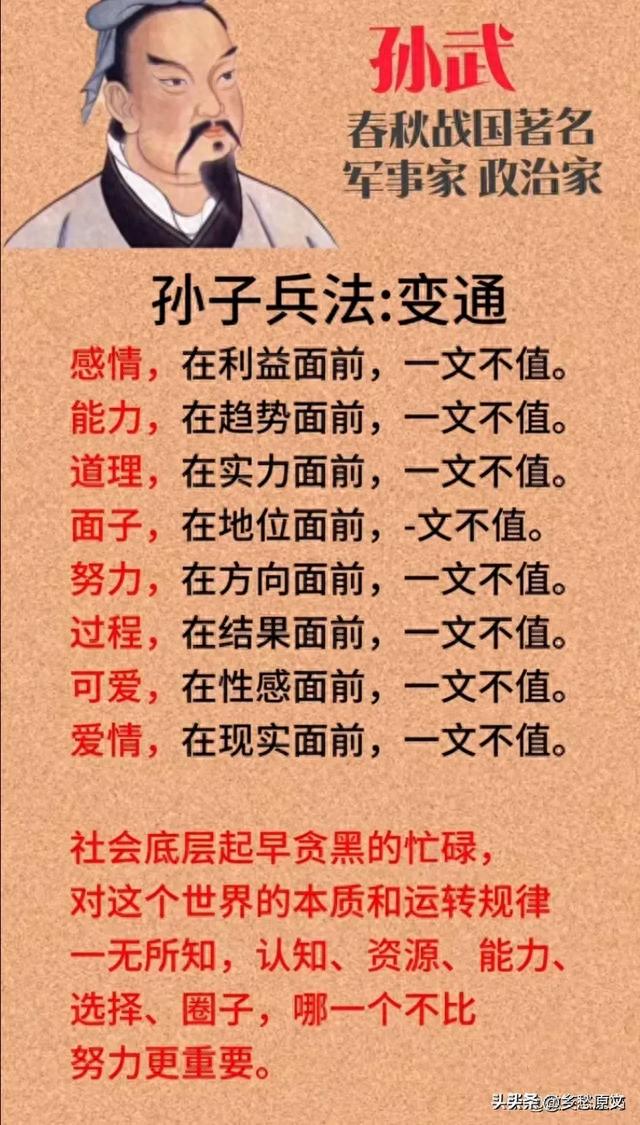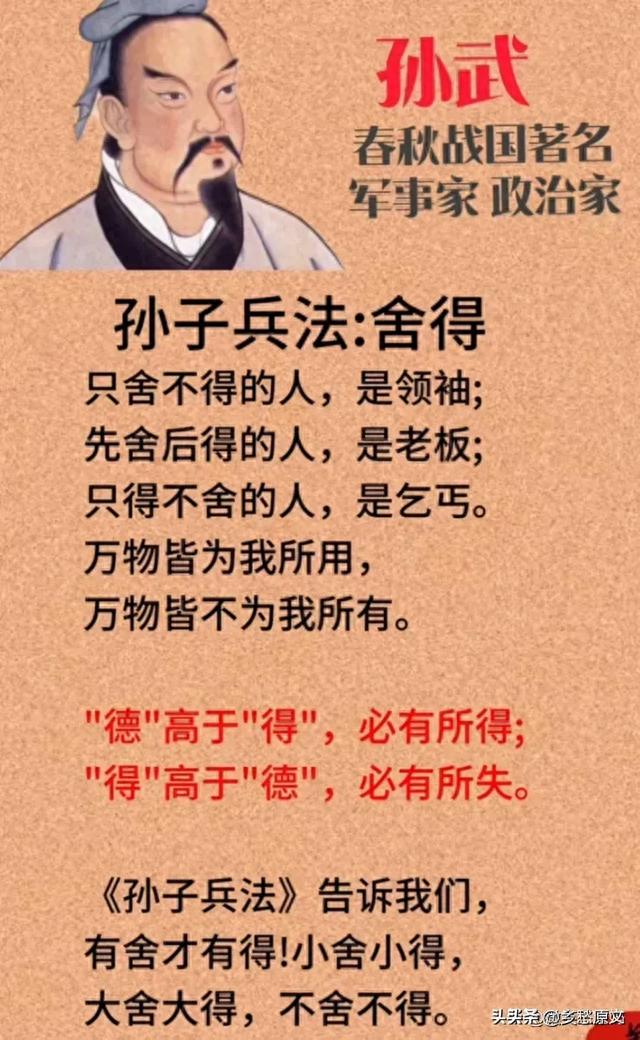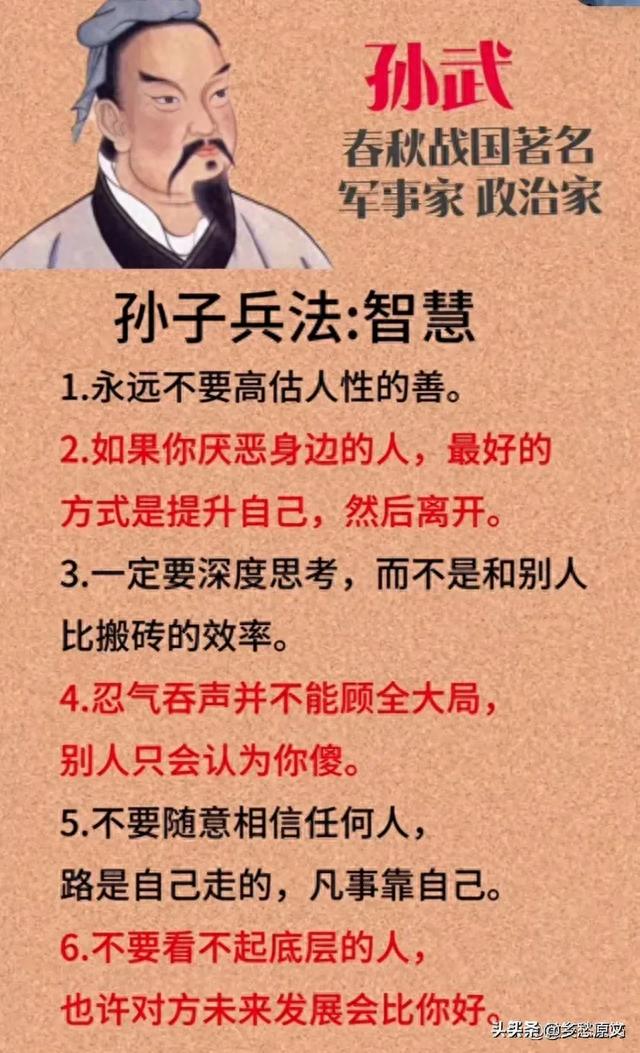子居:清华简十二《参不韦》解析(五) | 中国先秦史
清华简十二《参不韦》解析(五)
子居
【宽式释文】
参不韦曰:启,秉德毋比。德似山,汝乃渊,毋自高也;德似渊,汝乃山,毋自堙也。称以五德,和以五味,民以静,以自定也。
参不韦曰:启,勉德、勉义、勉法、勉长、勉固,是谓内基;勉圣、勉惠、勉刚、勉柔、勉和,是谓外基。
参不韦曰:启,觊盈、觊得、觊富、觊大、觊达而不宜,是谓内副;觊戏、觊溢、觊华、觊上、觊独,是谓外副。
参不韦曰:启,不可上也而上之,是谓内崩;不可下也而下之,是谓外崩。
参不韦曰:启,不可迩也而迩之,是谓内罚;不可远也而远之,是谓外罚。启,知其不宜也,以有益于其身而升由之,是谓内忧;知其宜也,以无益于其身而弗升由,是谓外忧。启,知其无罪,以害于其身而刑之,是谓不辜,内毁;知其有罪也,以有益于身而弗罚,是谓不刑,外毁。启,知其宜也,虽无益于身而升由之,是谓外屏;启,知其不宜也,虽有益于其身而罚之,是除秽章明,在罚弗当。启,内有乱德,是谓外讙;外有乱德,是谓内讙。
参不韦曰:启,闾率不德,橐忨不从。后秉德,启,毋自绌也。启,乃升正由宜,是谓外缓,以自达也;启,殃疾、戚忧、亡废,后秉德,启,乃稽诛罚戮,是谓内攘,以自除也。
【释文解析】
參不韋曰:𢻻(啟),秉悳(德)毋比,悳(德)巳(似)山,女(汝)乃𣶒(淵),毋自

(高)【六四】也。悳(德)巳(似)𣶒(淵),女(汝)乃山,毋自𡨾(垔)也。爯(稱)以五悳(德),和以五味,民以

(匡)以自定【六五】也〔六〕。
整理者注〔六〕:“巳,读为「似」。𡨾,读为「湮」。《说文》:「湮,没也。」《尔雅·释诂》:「湮,落也。」郭注:「沈落也。」犹谓「沉降」。简文以「山」、「渊」作喻,告诫启「秉德毋比」。称以五德,五德即「五则」,简四至五谓「帝乃用五则唯称」。矬,字后补,从矢,罜声,读为「匡」。”[1]“秉德毋比”盖是言所秉之德与其行事不要人为造伪,而当以反映实际情况为准。此节的“𡨾”字字形与春秋晚期《宋君夫人鼎》(《铭图》2222)中的“𡨾”字相近,差别在于清华简《参不韦》的“𡨾”字在土符上增加了人形饰笔,因此可推测清华简《参不韦》这个字形或即来源自春秋晚期而有所发展,很可能是战国初期、前期字形。清华简《参不韦》中,“味”字有三种字形,简02、简05、简17、简25皆书作“未”,简65、简87“味”字书作上未下日的“昧”字,简90、简99“味”字作左旨右未,三种写法并不混杂,故或可推测三部分的原书写时间有所不同。整理者隶定为“

”的字,疑即从知从王的“圣”字异体,见《碑别字新编·十三画·圣字》所引《齐比丘惠瑍造象》,此处可读为“静”,“静”与“自定”皆是道家常用概念,如郭店楚简《老子》甲篇:“知足以静,万物将自定。”《管子·内业》:“心能执静,道将自定。”《申子》:“名自正也,事自定也。”《尸子·分》:“执一以静,令名自正,令事自定。”《韩非子·扬权》:“故圣人执一以静,使名自命,令事自定。”《韩非子·主道》:“故虚静以待令,令名自命也,令事自定也。”马王堆帛书《十大经·名形》:“形恒自定,是我愈静。”于此当可见清华简《参不韦》在战国末期的改写者有着很明显的道家倾向。
參不韋曰:𢻻(啟),㝃(勉)悳(德)㝃(勉)宜(義)㝃(勉)

(法)㝃(勉)長㝃(勉)固,是胃(謂)內基。㝃(勉)𦔻(聖)【六六】㝃(勉)惠㝃(勉)

(剛)㝃(勉)𢘅(柔)㝃(勉)和,是胃(謂)外基〔一〕。
整理者注〔一〕:“㝃,字形与「字」同形,疑读为「勉」,勉励。此节以「内」、「外」相对。”[2]整理者似乎不是很喜欢标顿号,此段文字及下段文字明显应标顿号处,整理者释文皆未标出。书为“

”的“法”字字形与清华简《命训》、《五纪》相近,《五纪》的写法基本可以确定是继承自清华简《参不韦》,由此类推,则若清华简《命训》的这个“法”字没有在传抄中改变字形的话,那么其的作者很可能也是因看过清华简《参不韦》而受到的影响。对“德”、“义”、“法”的强调说明此段内容倾向于道家或法家,明显不是儒家思想,这一点可以比较于《管子·五辅》:“德有六兴,义有七体,礼有八经,法有五务,权有三度。”非常明显清华简《参不韦》此段的倾向甚至比《五辅》的作者在观念上距离儒家还要更远。之后的“刚”、“柔”更是来源于阴阳家的观念,因此可推知清华简《参不韦》此段体现出的倾向当是最接近阴阳家和道法家。“基”字写法与春秋晚期《子璋钟》(《集成》00114)的“基”字相近,这一点与前文提到的“𡨾”字情况很接近,盖同样说明原始清华简《参不韦》曾存在一个接近春秋晚期的版本。
參不韋曰:𢻻(啟),剴(愷)浧(盈)剴(愷)𠭁(得)剴(愷)

(富)剴(愷)【六七】大剴(愷)達而不宜,是胃(謂)內副。剴(愷)

(戲)剴(愷)溢剴(愷)芋(華)剴(愷)上剴(愷)蜀(獨),是胃(謂)外【六八】副〔二〕。
整理者注〔二〕:“剀,读为「恺」,《尔雅·释诂上》:「恺,乐也。」涅,读为「盈」。芋,楚简多用为「华」。副,读如字,训为「裂」或「析」。句意谓贪得务奢,财物荣华最终会离析散失。”[3]网友激流震川2.0提出:“简67 68 69'参不韦曰:启,剀盈、剀得、剀富、剀【67】大、剀达而不宜,是谓内副。剀戏、剀溢、剀华、剀上、剀独,是谓外【68】副。’整理报告将'剀’括读为'恺’,揆诸文义,似乎可读为'冀’,希求之意。几、岂关系密切,又《左传·哀公十六年》:'国人望君,如望岁焉,日月以几’,《释文》:'几,音冀,本或作冀。’”[4]网友ee继之指出:“'恺’'激流震川2.0’已读为'冀’,应该是正确的。也可以读为'觊’,觊觎、冀望的意思。参清华九《迺命一》简11'剀其有竝命’,'剀’即读为'冀’。”[5]所说皆是,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二十五:“难冀,居致反。《玉篇》云:'望也。’又作觊,《说文》:'觊,幸也。’”可证二读皆通,“剀”与“觊”同有声符“岂”,故相较于读为“冀”而言,读为“觊”略优。“富”字书作“

”,与楚简常见的上畐下贝不同,故很可能并非楚地写法。“盈”、“得”、“富”、“大”、“达”皆是内在的欲望,所以属于“内副”。笔者在《清华简十一五纪解析(之一)》[6]中已提到“'戏’训为虐,《尚书·西伯戡黎》:'非先王不相我后人,惟王淫戏用自绝。’《史记》引'戏’即作'虐’。”“溢”用为“泆”,二字通假[7]。“华”即浮华虚荣,《说文·华部》:“华,荣也。”“上”即占据更有利的位置而气势凌人,《国语·周语中》:“书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韦昭注:“上,陵也。”“独”即专断,《庄子·人间世》:“回闻卫君,其年壮,其行独。”《释文》:“崔云:'自专也。’向云:'与人异也。’郭云:'不与人同欲。’”“戏”、“溢”、“华”、“上”、“独”皆为外在表现,所以属于“外副”。
參不韋曰:𢻻(啟),不可上也而上之,是胃(謂)內朋(崩)。不可下也而下之,是胃(謂)【六九】外朋(崩)。
对比下文内容可推知,此处的“上”训为升,“上之”盖指拔擢,如升职、任命等,《易传·需卦·象传》:“云上于天,需,君子以饮食宴乐。” 《释文》:“干宝云:上,升也。”“下之”盖即指降职、免官等,《礼记·中庸》孔颖达疏:“下,谓贬退。”“内”、“外”则可以理解为朝、野。《国语·晋语八》:“伯华曰:'外有军,内有事。赤也,外事也,不敢侵官。’……祁奚曰:'公族之不恭,公室之有回,内事之邪,大夫之贪,是吾罪也。’”韦昭注:“内,朝内也。”
參不韋曰:𢻻(啟),不可(邇)也而

(邇)之〔三〕,是胃(謂)內

(罰)。不可遠也而遠之,是胃(謂)外【七〇】

(罰)。
整理者注〔三〕:“邇,读为「迩」,与「远」相对。”[8]“

”字又作“𤞷”形,西周金文习见,有时还与“𡎐”形讹混,清华简十《四告·满告》中则作“

”,清华简其它各篇中的“迩”则多作“逐”形或从“逐”形的字。清华简《参不韦》势必不能早到西周时期,因此比较于清华简十《四告·满告》当可推测,清华简《参不韦》所保留的“

”形来源盖与《四告·满告》时间大致相当,笔者在《清华简十四告·满告解析》[9]中已提到:“《四告·满告》的成文时间盖是在春秋后期初段左右,且作者可能是管仲后裔。”前文解析内容也已提到清华简《参不韦》的主体部分盖成文于春秋前期后段、末段之交的齐、杞文化融合背景,二者的时间点和地域范围都正相邻近,由此也可以勾勒出从“

”到“

”再到“逐”的字形演变过程。《逸周书·大匡》:“不远群正,不迩谗邪,汝不时行,汝害于士。”《晏子春秋·内篇谏下·景公嬖妾死守之三日不敛晏子谏》:“今君不道顺而行僻,从邪者迩,导害者远,谗谀萌通,而贤良废灭,是以谄谀繁于间,邪行交于国也。”皆可与清华简《参不韦》此节相参看,由此即可见清华简《参不韦》与《逸周书·大匡》和《晏子春秋》持论相近之处。
𢻻(啟),智(知)亓(其)不宜也,以有𠍳(益)於亓(其)身而陞(徵)由之〔四〕,是胃(謂)內𢝊(憂)。智(知)亓(其)宜【七一】也,以亡(無)𠍳(益)於亓(其)身而弗陞(徵)由,是胃(謂)外𢝊(憂)。
整理者注〔四〕:“陞,读为「征」。征由,征用。”[10]“升”完全可以读为原字,而无须读为“征”,《国语·周语中》:“若佐新军而升为政,不亦可乎?”《国语·晋语五》:“其主朝升之,而暮戮其车,其谁安之?”《国语·晋语九》:“昔先主文子少衅于难,从姬氏于公宫,有孝德以出在公族,有恭德以升在位。”《国语·楚语上》:“如是而又使以象梦旁求四方之贤,得傅说以来,升以为公。”《国语·齐语》:“设之以国家之患而不疚,退问之其乡,以观其所能而无大厉,升以为上卿之赞。”皆可证,因此“升由”犹言“升用”,《呂氏春秋·观世》:“不得休息而佞进,今之世当之矣。”高诱注:“佞谄者进而升用也。”即“升用”辞例。《尚书·尧典》:“帝曰:畴咨若时登庸?”孔传:“庸,用也。”而升、登通假互训[11],可见“登庸”亦犹言“升用”。相对于清华简《参不韦》所言“内忧”、“外忧”,传世文献则有《管子·戒》:“妾人闻之,君外舍而不鼎馈,非有内忧,必有外患。”《管子·侈靡》:“吾闻之先人,诸侯舍于朝不鼎馈者,非有外事,必有内忧。”《国语·晋语六》:“幸以为政,必有内忧。且唯圣人能无外患,又无内忧,讵非圣人,必偏而后可。……且唯圣人能无外患又无内忧,讵非圣人,不有外患,必有内忧。盍姑释荆与郑以为外患乎。”《左传·成公十六年》:“唯圣人能外内无患。自非圣人,外宁必有内忧。盍释楚以为外惧乎。”《左传·昭公二十三年》:“民无内忧,而又无外惧,国焉用城。”《管子》与《国语》、《左传》编撰者的关系明显可见,而清华简《参不韦》此节虽然用法略有不同,但用词相近则不难判知。再者,“知其不宜也,以有益于其身而升由之,是谓内忧。”于先秦最著名的事例即齐桓公与易牙、竖刁等人事,《管子·戒》:“管子遂卒。卒十月,隰朋亦卒。桓公去易牙、竖刁、卫公子开方。五味不至,于是乎复反易牙。宫中乱,复反竖刁。利言卑辞不在侧,复反卫公子开方。桓公内不量力,外不量交,而力伐四邻。公薨,六子皆求立,易牙与卫公子,内与竖刁,因共杀群吏而立公子无亏,故公死七日不敛,九月不葬。”由于笔者推测的清华简《参不韦》主体成文时间在春秋前期后段、末段之际,而这个时间点就意味着《参不韦》作者很可能亲历齐桓公亡故之事,因此不排除此节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因此事而作。
𢻻(啟),智(知)亓(其)亡(無)辠(罪),以魝割(害)於亓(其)【七二】身而

(罰)之〔五〕,是胃(謂)不古(辜),內毀。智(知)亓(其)有辠(罪)也,以有𠍳(益)於身而弗

(罰),【七三】是胃(謂)不刑,外毀。
整理者注〔五〕:“魝,「割」字讹体,读为「害」。”[12]清华简《参不韦》的“智”字皆不从“日”而从“皿”,整理者无论是在照片释文中还是在释文注释部分都未加体现,甲骨文“智”字作“

”,《说文》言“智”字从“白”且古文从丘作“

”,《汗简》卷二“智”字作“

”、“

”,黄锡全先生《汗简注释》:“廿即口之变……古从皿从血混同,《说文》所从的𠀌和石经所从的血均为皿变……古文字中的智多从𤮺作……王国维云:'下从𤮺,乃象盛物之器,绝非白字……皿亦盛物之器也……此字或从日,或从皿,其故亦同(《魏石经残石考》)。’”网友质量复位提出:“简72—73'以魝于其身而罚之’,整理者认为'魝’是'割’字讹体,读为'害’。按,整理者读'害’可信,但'魝’恐非误字。该字见于《说文》,《说文》刀部:'魝,楚人谓治鱼也。从刀、从鱼。’桂馥义证:'治鱼即剖鱼。’《广雅·释诂二》:'魝,割也。’'魝’可能是'割鱼’之'割’的专字。上古音'魝’'割’均属见纽月部,'害’属匣纽月部。出土文献中可见'舝’与'蓟’通假(《战国时代各系文字间的用字差异现象研究》P39),'蓟’从魝声;而楚简中常用'舝’表示'害’(《简帛古书通假字大系》P81)。再者,《说文》云:'魝……读如锲。’而'锲’'害’俱从丯声。”所说当是,原字可通则不应因自身偏好而任意使用通假,而当尽量保留原字原貌,这是基本原则。《管子·明法解》:“明主虽心之所爱,而无功者不赏也;虽心之所憎,而无罪者弗罚也;案法式而验得失,非法度不留意焉;故明法曰:「先王之治国也,不淫意于法之外。」”比较即可见清华简《参不韦》的倾向与管子学派论述的相近性。
𢻻(啟),智(知)亓(其)宜也,唯(雖)亡(無)𠍳(益)於身而曾(增)

(由)之,是胃(謂)【七四】外苹(屏)〔六〕。
整理者注〔六〕:“曾,读为「增」,《尔雅·释言》「增,益也。」胄,读为「由」,用。苹,读为「屏」,屏障。”[13]“益由之”明显不辞,故整理者读“曾”为“增”训为“益”当不确。登,曾相通[14],故笔者认为“曾由”即前文的“升由”。“虽无益于身而曾由之”是明显的尚贤观念,如《墨子·尚贤下》:“于先王之书《竖年》之言然,曰:'晞夫圣武知人,以屏辅而身。’此言先王之治天下也,必选择贤者以为其群属辅佐。”
𢻻(啟),智(知)亓(其)不宜也,唯(雖)有𠍳(益)於亓(其)身而

(罰)之,是敘(除)

(穢)章𥁰(明),【七五】才(在)

(罰)弗尚(當)〔七〕。
整理者注〔七〕:“唯,读为「虽」。叙,读为「除」、

,读为「秽」。尚,读为「当」;一说读为「常」或「赏」。此句盟(明)、尚(当)为韵,阳部。”[15]所言“唯,读为「虽」。”当注于前文以涵盖此处对应文句,不知整理者何以不在之前出注而注在此处。依清华简《参不韦》此节的行文模式,对应前文“是谓外屏”,本段文字的“是”字后似也当有对应文句,而比较前文的“以有益于其身而升由之,是谓内忧”,则“虽无益于身而升由之”后应言“是谓内屏”,疑抄手在此处有所脱漏讹误。对应前文的“还祥不当”,此处的“在罚不当”句意应相近,盖是指即是原有天罚也不会承当。“除秽”一词,先秦传世文献可见见于《晏子春秋·外篇第七·景公使祝史禳彗星晏子谏》:“且天之有彗,以除秽也。君无秽德,又何禳焉?”(同样的内容又见《左传·昭公二十六年》)《文子·九守》:“除秽去累,莫若未始出其宗,何为而不成。”“章明”一词,先秦传世文献可见于《墨子·尚贤中》:“则此言圣人之德,章明博大,埴固,以脩久也。”《国语·晋语八》:“物莫伏于蛊,莫嘉于谷,谷兴蛊伏而章明者也。”《国语·越语下》:“兵胜于外,福生于内,用力甚少而名声章明。”《管子·侈靡》:“章明之毋灭,生荣之毋失。”《管子·版法解》:“父慈子孝,兄爱弟敬,礼义章明。”《吕氏春秋·诬徒》:“学业之章明也,道术之大行也,从此生矣。”《文子·道原》:“雄牡有名,有名者章明也。”比较可见,两个词都同见于《文子》,说明“除秽章明,在罚不当”这句内容的形成时间很可能与《文子》较接近,也是在战国末期形成的,因此这句话很可能是战国末期的那位改写者所加入的内容。
𢻻(啟),內有𡄹(亂)悳(德),是胃(謂)外雚(歡)。外有𡄹(亂)悳(德),是胃(謂)內嚾(歡)〔八〕。【七六】
整理者注〔八〕:“雚,读为「欢」。句意谓内有乱德则外欢,外有乱德则内欢。”[16]笔者前文解析已言内、外盖是指朝、野,对于夏后启而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那么如果按整理者的解释读“雚”为“欢”,朝堂有乱德,乡野必然会因此有池鱼之殃,何欢之有?乡野有乱德,为什么朝堂会欢?整理者注释都没有给出任何解释。网友质量复位提出:“按,'雚’可读为'嚾’,而'嚾’可如字读。'嚾’有喧嚣、喧哗的意思,与'乱’意近。《荀子·非十二子》:'世俗之沟犹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嚾’'讙’可能是一字异体。'讙’有喧哗的意思。”[17]但这样仍然难以解释为什么“内有乱德”不是“内讙”而是“外讙”,“外有乱德”不是“外讙”而是“内讙”。笔者认为,若考虑到前面多个排比句都是先言内后言外,只在笔者所提到的“这句话很可能是战国末期的那位改写者所加入的内容。”那句开始才变成先言外,故值得考虑很可能是改写者在改写时导致了误书,“虽无益于身而升由之”是从乡野选拔至朝堂,因此实际上原始版本很可能当是“是谓内屏”而非现在所见的“是谓外屏”,盖改写者抄写讹误,由此影响到了下面的此节,此点前文解析已言。也就是说,“内有乱德,是谓外讙。外有乱德,是谓内讙。”很可能原当为“内有乱德,是谓内讙。外有乱德,是谓外讙。”
參不韋曰:𢻻(啟),

(呂)頪(律)不𠭁(得)〔一〕,厇(度)

(願)不從,句(后)秉悳(德)。𢻻(啟),毋自絀(黜)也。𢻻(啟),乃曾(增)【七七】定

(由)宜,是胃(謂)外緩(援),以自達也〔二〕。
整理者注〔一〕:“

,从门,肤声,「闾」字异体,读为「吕」。頪,「类」字古体,读为「律」。吕律,指六吕六律。六吕指大吕、夹钟、中吕、林钟、南吕、应钟,六律指黄钟、太簇、姑洗、蕤宾、夷则、无射。”[18]“

”字又见《

丘为𩿊造戈》(《集成》11073)、《是立事岁戈》(《集成》11259),《䣄王卢》(《集成》10390),《集成》皆定为春秋晚期器,《春秋·襄公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闾丘来奔。”杜预注:“二邑在高平南平阳县,东北有漆乡,西北有显闾亭。”《水经注·洙水》:“洙水又西南,迳南平阳县之显闾亭西,邾邑也。《春秋·襄公二十一年·经》书'邾庶其以漆、闾丘来奔’者也。杜预曰:'平阳北有显闾亭。’《十三州记》曰:'山阳南平阳县又有闾丘乡。’《从征记》曰:'杜谓显闾、闾丘也。今按漆县在县东北,漆乡东北十里,见有闾丘乡,显闾非也。’”是闾丘即在鲁之南,邾之西南。“

”字又见于齐陶文,据《临淄齐故域内外新发现的陶文》:“战国时期,齐城门有称'高闾’者,由陶文可知,齐城门春秋名'高

’,战国早中期称'高

’、'高

’,以后则称'高闾’。”[19]由此可推知“

”形为春秋晚期齐、鲁、徐文化区的写法。笔者在《先秦文献分期分域研究之二
实词篇(一)》[20]已指出《逸周书·尝麦》约成文于春秋前期前段,因此可推知清华简《参不韦》的主体成文时间盖即在春秋前期前段和《集成》所言春秋晚期之间,这也就印证了笔者前文解析内容所分析的清华简《参不韦》主体盖即成文于春秋前期后段、末段之际。先秦两汉文献中“律吕”一词习见,但称“吕律”的辞例则无一见,故整理者读“

頪”为“吕律”之说很明显成立的可能性极小。笔者认为,“类”、“率”相通[21],故“

頪”可读为“闾率”,《逸周书·尝麦》:“乃命百姓,遂享于家,无思民疾,供百享归祭,闾率里君,以为之资野。”朱右曾《集训校释》:“率若连率之率,闾率里君,《周礼》谓之闾胥里宰。”是闾率犹言闾长。“得”、“德”相通[22],故“不得”可读为“不德”,《逸周书·大聚》:“合闾立教,以威为长。”《周礼·地官·闾胥》:“闾胥,各掌其闾之徵令。以岁时各数其闾之众寡,辨其施舍。凡春秋之祭祀、役政、丧纪之数,聚众庶;既比,则读法,书其敬敏任恤者。凡事,掌其比觵挞罚之事。”可见闾长行政主要是以罚立威,而不是以德服众,所以有“闾率不德”。“厇”当如前文“

”字读为“橐”,“

”为“忨”字异体,《广雅·释诂二》:“忨,贪也。”王念孙《疏证》:“《尔雅》:'懊,忨也。’'愒,贪也。’《说文》:'玩,贪也。’昭元年《左传》'翫岁而愒日’,杜预注云:'翫、愒,皆贪也。’《晋语》作'忨日而㵣岁’。昭二十六年《左传》'玩求无度’,服虔注云:'玩,贪也。’怃、翫、玩,并通。”《国语·晋语八》:“今忨日而㵣岁,怠偷甚矣。”韦昭注:“忨,偷也。”“

”训为贪、偷于此句皆通,训为“偷”于义较佳,故“橐忨”可以理解为藏匿苟且,“橐忨不从”可以理解为不容忍放任藏匿苟且之行。
整理者注〔二〕:“绌,读为「黜」,贬退。增定由宜,与简七四至七五「虽无益于身而增由之,是谓外屏」有关。缓,读为「援」,助。自达,自我通达。”[23]“闾率不德,橐忨不从”明显有重刑罚而非宣教的法家倾向,故此节言“后秉德,启,毋自绌也”即是以刑罚为德而以教化为自贬自抑。“曾”当读为“升”而非读为“增”,前文已言。“定”读为“正”[24],训为正直,《鬼谷子·摩篇》:“正者,直也。”《吕氏春秋·君守》:“有准不以平,有绳不以正。”高诱注:“正,直。”“缓”字完全可以读为原字,训为宽舒,慧琳《一切经音义》卷十二:“皮缓,户满反,《尔雅》:'缓,舒也。’顾野王云:'宽也。’”因前文解析所分析的情况而言,此处的“外缓”疑也本当作“内缓”。
𢻻(啟),央(殃)疾慼(戚)𢝊(憂)亡

(廢),句(后)秉悳(德)。𢻻(啟),【七八】乃旨(稽)𠁁(鬭)

(罰)𣩍(戮),是胃(謂)內𤕦(攘),以自敘也〔三〕。
整理者注〔三〕:“旨,读为「稽」,《说文》:「稽,留止也。」清华简《五纪》简一〇七「肆虐廼旨」,「旨」读为「稽」,训止,可证。𠁁,字在常见字形上益二「口」形,读为「鬭」。𤕦,与「援」相对,读为「攘」。自叙,与「自达」相对,疑读为「自除」。”[25]“旨”字上部的人形面左,篇中“指”字同样人形面左,这与古文字中“旨”字人形一般面右不同,同样人形左面的“旨”字又见于《上曾大子鼎》(《集成》02750)、《䣄令尹者旨荆卢》(《集成》10391)及《说文》古文。上曾大子鼎出土于山东临朐县嵩山泉头村墓葬(M乙:一),《集成》定为春秋早期器;䣄令尹者旨荆卢出土于江西靖安县李家村,《集成》定为春秋器。由此可见,清华简《参不韦》的“旨”字写法体现出一种界于齐、徐之间的春秋时期书写特征,而临朐正近于杞国故地,也可以与笔者前文解析内容推测清华简《参不韦》的主体盖是形成于齐文化与杞文化的融合相印证。网友ee提出:“简79:'乃稽𠁁罚戮’,'𠁁’,整理者读为'鬭’,语义不谐。按,'𠁁’应读为'诛’,如'𠁁’为'鬭’之声符,'鬭’端纽侯部,'诛’亦端纽侯部,二字古音很近。《礼记·曲礼上》:'以足蹙路马刍,有诛。齿路马,有诛。’郑注:'诛,罚也。’”又言:“稽,整理者引《说文》训爲留止,按,应该是考察的意思。《周礼·地官·县正》'既役,则稽功会事而诛赏。’”所说皆当是。“罚戮”一词,又见《开元占经·石氏中官·梗河占》引《黄帝占》曰:“梗河三星,天锋;天之剑戟,主于罚戮。”严可均《黄帝占叙》:“此书占八谷,有太阴乘寅、乘卯、乘辰等占,而又别有太岁,多非后世语。其占少微有『闻如孔子,巧如鲁般』二语,知撰书人在孔子后,盖六国时依托也。”战国时托名黄帝的学说多出齐文化区,因此可推知《黄帝占》很可能是一种齐地星占汇编,《三国志·董昭传》:“董昭字公仁,济阴定陶人也。……太和四年,行司徒事,六年,拜真。昭上疏陈末流之弊曰:……以毁訾为罚戮,用党誉为爵赏。”由此也可见言“罚戮”很可能是齐文化影响区的措辞。
[1]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贰》第127页,上海:中西书局,2022年10月。
[2]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贰》第128页,上海:中西书局,2022年10月。
[3]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贰》第128页,上海:中西书局,2022年10月。
[4] 简帛论坛:/forum/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12766&pid=30544,2022年12月2日。
[5] 简帛论坛:/forum/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12766&pid=30548,2022年12月2日。
[6] 中国先秦史网站:,2022年1月9日。
[7] 《古字通假会典》第450页“溢与泆”条,济南:齐鲁书社,1989年7月。
[8]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贰》第128页,上海:中西书局,2022年10月。
[9] 中国先秦史网站:,2021年1月14日。
[10]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贰》第128页,上海:中西书局,2022年10月。
[11] 《古字通假会典》第33页“登与升”条,济南:齐鲁书社,1989年7月。
[12]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贰》第128页,上海:中西书局,2022年10月。
[13]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贰》第128页,上海:中西书局,2022年10月。
[14] 《古字通假会典》第33页“登与增”条,济南:齐鲁书社,1989年7月。
[15]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贰》第128页,上海:中西书局,2022年10月。
[16]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贰》第128页,上海:中西书局,2022年10月。
[17] 简帛论坛:/forum/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12766&pid=30547,2022年12月2日。
[18]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贰》第129页,上海:中西书局,2022年10月。
[19] 《文物》1988年第二期。
[20] 中国先秦史网站:,2016年7月3日。
[21] 《古字通假会典》第537页“类与率”条,济南:齐鲁书社,1989年7月。
[22] 《古字通假会典》第408页“德与得”条,济南:齐鲁书社,1989年7月。
[23]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贰》第129页,上海:中西书局,2022年10月。
[24] 《古字通假会典》第60页“正与定”条,济南:齐鲁书社,1989年7月。
[25]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贰》第129页,上海:中西书局,2022年10月。
- 0000
- 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