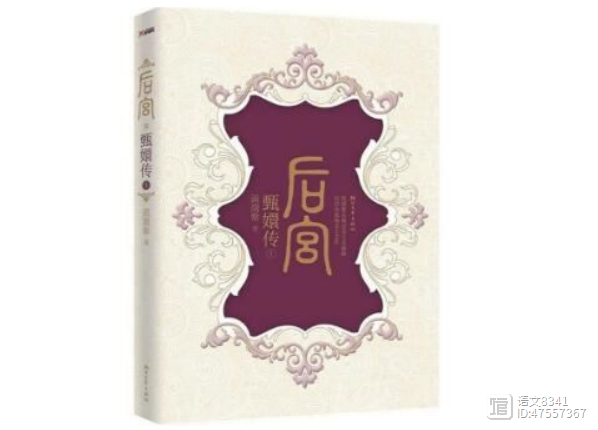七 敌 营 十 五 年——营救杨靖宇将军的弟弟

在此期间,我还将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指挥兼政治委员杨靖宇将军的弟弟杨树田营救出狱。
那是在日本投降后不几天,我党另一部门的地下工作者、我的老同学范纪曼到军法处找我。他说有两个同志被关押在提篮桥监狱,我们要趁此时局混乱之机将他们营救出来。
一天,我们二人都穿着有少将军衔的军服同乘我的汽车驶往提篮桥监狱。我指着范纪曼对典狱长沈冠三说,这位是刚从重庆来的范高参,他是专为接在押人李一鸣和杨树田来的。我向他说明:“这件事是要我们行动总队司令部军法处会同办理的, 我特意随同范高参前来,请老兄照办。”沈典狱长听说是重庆方面来要员,便诚惶诚恐地答应, 并立即命令狱吏赶快查一下。
不多时,狱吏报告说:“这个案子是上海日军司令部办的苏联谍报案,李一鸣已于前几天被日本人要去了, 只有杨树田一个人了。”我们说: “那就接他一个人吧。”片刻,杨树田扛着破被子被看守带到台阶下边,我们都走出了办公室。范纪曼抢上一步走近杨树田低声用俄语说:“若是他们问,你就说是我的部下。”然后, 他回过头对我说:“老李,人来了, 咱们带走吧。”我说:“好!”沈典狱长面有难色:“长官,你们领去在押犯人,要写提人收据啊!”范纪曼随机应变,装出国民党军人那种蛮横的凶相,用训斥的口吻说:“日本已经投降了,你还要他妈 的什么收条!你还想帮日本人吗?真是混蛋!⋯⋯”
沈冠三害了怕,连忙说:“是!好!我遵命。可是, 没有提人的手续,我也不好向上面交待呀!请长官原谅,在提人收条上签个字就行了。”此时,我急于把杨树田领出监狱,我考虑若搞僵了就不好办了,便打圆场地说:“提人的收据由我来写吧。”我签完字后,沈典狱长和几名狱吏像送客人那样送我们出了监狱大门。
此事,我曾向张执一汇报过。他认为,营救同志是应该的,但总有点危险。事后,我自己也曾想,假如国民党政府接收监狱后追问此事,是很麻烦的,肯定会对我的潜伏工作带来不利的影响。有一段时间,我常为此事而担心,好在一年多后无人过问, 我心里才如一块石头落了地。
打入军统内部 1945年8月下旬,党中央决定我八路军、新四军集中力量先解放东北,因此上海起义作罢,上海由国民党接管统治,我党仍处于地下秘密状况。当我们正在研究继续在上海潜伏下来,还是参加解放东北的战斗时,我以前认识的律师余祥琴由浙江回沪,来到我的家中。他劝我不要离开上海。他说:“我以前是军统领导的沪郊指挥站的负责人,你如能将警察局的人员拉一些给我工作,我就可以帮你混进去。”“怎么混进去呢?”我问。“有办法。沪郊指挥站曾报了些吃空饷的假名字,可以给你顶一个, 就说是你的化名。”“这太危险吧,而且会连累你呀!”余祥琴镇定自若地说:“不要紧,军统拉汪伪组织人员使用,是叫'运用人员’,不是正式参加军统组织,不会认真查对的。”
他还一再表示,一定保守这一秘密,如有纰漏,他自己也吃不消。我向他表示考虑考虑再说。我将余祥琴与我谈话的内容向刘人寿、张执一作了汇报。几天后,他们通知我,说党组织已研究决定让我将计就计, 打进军统去,进行工作。以后,余祥琴又来找我,我就向他表示, 如果他能保证不出乱子,我可以留在上海,跟着他工作,希望他可要够朋友。他百般许诺,说不会出错。
余祥琴是8月26号回到上海的。此后,军统特务陆续来到上海,他们成为国民党政府接收上海的先遣部队。在国民党政府未正式接收之前,这帮特务还是在伪组织军警维持治安的保护伞下活动。军统在上海的办事处,设在杜美路七十号杜月笙的公馆里。以戴笠为首的军统大特务龚仙肪、李崇琦、王新衡、沈维翰、寥化平等相继来到上海。戴笠刚到上海时,经常住在金神父路十一号唐生明家中。后来军统上海办事处给戴笠置备了四五处公馆。
9月中旬,军统在杜美路召开上海办事处纪念周会议, 我接余祥琴的电话也参加了这个会。戴笠主持会议并讲了话。他除了大吹大擂军统在八年抗战中的战功之外,还告诫大小特务们要肃清“奸党”, 也就是要竭尽全力阻挠我党我军接收,由他们来抢劫胜利果实。我当时一方面听他大放厥词,以了解其动向;一方面注意他的言谈举止,以摸清其习性。戴笠这个军统头子的阴险狡诈果然名不虚传, 他时而凶神恶煞,时而道貌岸然,变化多端,反复无常。余祥琴对我说:“有机会领你见戴先生谈谈。”我当时的心情是想见又不想见他。想见,是考虑可以进一步了解这个大特务头子到底有什么本领和特点;不想见, 是担心与他直接接触,如稍有不慎,就会被其识破我的真面目。
一天,余祥琴约我去见他的老师、青帮头目、金融界大亨杜月笙。我们同杜谈不多时,戴笠来了。余即向戴介绍我。戴笠头一句话就说,我知道你。听余祥琴说过,你能干, 你在东北组织过抗日义勇军, 打进南京伪组织后为党国做了不少工作。我说,那是戴先生领导的好。他接着说,你在陈公博旁边工作,没有被李士群的七十六号发现,能混下来,就算有办法,不容易呀!“那是组织上领导的好,托戴先生的福!”我想不便多谈下去,随即说:“戴先生、杜先生,你们工作忙,不打扰了,以后再请戴先生和杜先生指教, 我告辞了。”
我打进军统之后,开始是以余祥琴的“沪郊指挥部”为掩护,随余参加他们逮捕、审讯汉奸的工作。由于常与特务们接触,我了解到不少有关军统的人事、组织、特务活动以及国民党接收上海市的各种情况。后来,军统上海区改组,余祥琴被任命为军统上海区第二站站长。此站下分三组: 第一组是政治组,专搞我党的情报;第二组是社会组,专搞上海社会动态, 即每日发生的重大事情;第三组是经济组,专门搜集上海经济界的情况。余祥琴推荐我担任第二组组长。
我逐步深入魔窟,利用职权之便,直接看到军统对所属区、站的指令、通报及通知等重要文件。我择其有价值的文件交给我地下党的负责同志看,从而使我党了解到军统特务们是如何注意我们的活动,以及他们将怎样监视、侦察、追踪某人或某事等等。这对于保卫我党我军和进步群众的安全,防止敌人破坏,避免或减少革命事业的损失,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在此期间,审讯汉奸对军统来说只是临时性的工作。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忙于重新建立上海特区和各省市的军统组织,以对付我党我军,破坏和谈,发动内战。其次, 便是改编伪军组织,建立交警队,以控制主要铁路、公路。他们还不遗余力地大搞劫收,即借逮捕审讯汉奸之机,搞“五子登科”。
日本投降后,大约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国民党政府全靠汪伪军警维持上海的治安。直到10月上旬,重庆的接收大员们以及那些被日军打得跑了很远的“国军”,才陆续乘美国飞机飞来上海。这些人涌入敌伪占领区后,各显神通,大抢特抢洋房、汽车、金条、美钞和汉奸的小老婆。他们花天酒地,吃喝膘赌,把一个本来就腐败不堪的上海,弄得更加乌烟瘴气,比沦陷时还糟糕!难怪老百姓气愤地说:“什么接收,简直是劫收!”美国兵们更是神气活现,坐着吉普车在大街上横冲直撞,撞伤人、轧死人的事件时有发生。美国兵不但追逐街头的“摩登女郎”,对行路的良家妇女也肆意调戏。老百姓叫苦说:“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前门驱出一条狼,后门进来一只虎。”
我被余祥琴推荐担任军统上海区第二站第二组组长后,余专为我安排了一所房子办公。我不常去那里,隔几天去看看文件。我把原伪警察局各分局司法股的人员拉了十多位,要他们把每天社会上发生的重大事件报来。按这个组的原定任务来说,我以为这样做满可以应付得过去。哪里知道,并不能满足区里的要求。比如某日某地发生聚众抢米事件,只把事件发生的情况报上还不行,还必须查出事件发生的起因和背景,也就是说,要指出是什么人在背后策动的。
这就麻烦了。我感到达个差事不好干。我虽然潜入敌占区从事情报工作多年,但掩护职业一直是上层政府的公职,容易把本职工作完成,并可以利用职权和机会, 去搜集我党需要的情报资料。现在不是这样了, 这个职位是给敌人以情报资料.这是我不情愿干的事情,所以军统上海区几次指责我这个组的工作没有成绩。在这种情况下,地下党的领导曾与我商议是不是编些假的,或过时的,或似是而非的情报去应付他们呢?我说,不能那样做。我的想法是,宁可让他们认为我对这个工作无知无能,也不能让他们抓住什么把柄。
与此同时,我对余祥琴说,我在这方面既无线索又无经验,我拉过来的原伪警察局人员是搞刑事案件的,对此工作也是外行。尽管余祥琴说过,军统对拉进汪伪组织的人员是利用,不会认真审查,可是军统对我这样不为他们卖力的人,不能不产生怀疑。余祥琴倒好说,因为我们是老朋友, 经过请客送礼,总算能周旋过去, 而督查处和军法处对我盯得很紧,进行秘密审查。
我查觉到军统对我在进行侦察,但不知道是怎样引起他们怀疑的。事后我才知道,军法处的沈维翰与余祥琴在审讯汉奸当中,因争权夺利发生了矛盾。我是余祥琴拉过来的人,沈维翰当然在我身上找碴子以对付余祥琴了。他们在侦察中,了解到我的弟弟李春芳和我的爱人孙静云曾因共产党抗日嫌疑而被捕过。此外,余祥琴平时忽而叫我“李渊”、忽而叫我“赵和锋”,也是他们引起怀疑的原因。
沈维翰在找到一些蛛丝马迹之后,便以此作文章。他拍电报给去北平部署工作的戴笠,简陈案由,请求批准扣押我。戴笠复电的内容大意是: 仙肪、维翰两兄,函悉。李时雨参加本局工作成绩如何?希详查再核,目前不可逮捕也。戴笠为何有这样的复电呢?后来我才知道,他在北平接到电报后,顺便问在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任督察长的李国章,打听我是怎样一个人。李是我们的人,当然替我说了一番好话,加之戴笠见过我,他对我没有什么不好的印象,所以没有批准立即逮捕我。然而,沈维翰等仍不死心,继续进行侦察,我也提高警惕继续坚持工作。
1946年3月上旬,戴笠因飞机失事摔死。戴笠死后,军统特务内部相互倾轧更为加剧。那些嫡系特务对余祥琴开始找麻烦,对我则一再指责工作没有成绩,并继续暗中侦察。我早就有所察觉, 张执一也从另一方面得到情报,获悉军统特务在秘密侦察并随时准备逮捕我。所以,当我提出撤离上海时,张执一便立即同意了。他除了安排一位交通员负责随时准备送我的家属去苏北外, 还指示我到东北找陶铸同志接关系,由他分配工作。
可我怎样才能比较安全地离开上海呢?同余祥琴说明, 公开撤离?假如他不同意,那是会打草惊蛇的,只有秘密撤走。但用什么办法掩护才能更安全地撤走呢?我想起我的老师王抚洲在南京任直接税总局局长。万不得已, 我是不愿找他想办法的,因为听说他与戴笠很要好,他又是青年党人,同他拉近了还是不能跳出特务的圈子。此时,为了安全撤走。我也只好利用一下这个关系了。
到南京后,我找到了王抚洲,多年不见,彼此十分亲热。畅叙八年抗战阔别之情以后,我提出求他找工作,要护照。王抚洲很热情地说:“你若仍在军统工作,我可以托唐纵照顾你,唐是军统主要负责人之一,戴笠死了, 他说话一样有力,你若是愿意去东北工作。我可以给你安排当直接税局分局长。”我说:“我急于回家乡东北工作。”我提出最好是委我为营口分局局长,因为我的同乡同学王家善师长在那个地方驻防,会得到他的照应。王抚洲答应了我的要求,并说, 正好直接税东北局局长张维在此地。他当即找到张维与我见面。张维说营口准备设分局,他叫我去沈阳等候,委我任营口分局局长一职。王抚洲当即命令直接税总局办公室给我开了护照,交我带回上海。
- 0000
- 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