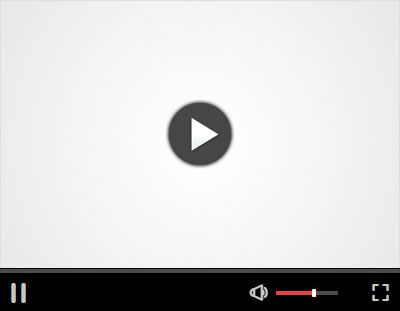韦胤宗丨中西学术视域中的“文献学”、“文本学”和“书籍史”
注:本文发表于《文献》2023年第3期,此为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韦胤宗老师授权发布!
中西学术视域中的“文献学”、“文本学”和“书籍史”
韦胤宗内容摘要:以书籍与文献为研究对象的“文献学”在中国与西方皆有非常悠久的传统。西方对于书籍与文献的研究最初以著录为主,名为bibliography,相当于中国传统的目录学;而西方现代的bibliography意义较广,包含书目题跋的编制、书籍生产过程和背景的考察、书籍形制的分析和文本的研究等内容,基本涵盖了中国的版本目录学、校勘学和出版史等研究领域。同时西方又有以整理和阐释经典文本为鹄的、以语言文字为主要研究对象的philology,相当于中国传统的小学。中国现代学科设置中的“文献学”包括以上两大方面的内容,因此“文献学”的英文译名应该是“bibliography and philology”。二十世纪中叶以后,西方学术界又陆续兴起文本学、书籍史等新领域,给书籍与文献的研究带来新的方法与视野,这些新的研究路径渐次传入中国,与中国本土的文献学相结合,使我国的文献学研究步入新的阶段。关键词:文献学 书志学 语文学 文本学 书籍史
中国与西方皆有非常悠久的文献学研究传统,但是,中国学者对于西方古典文献学的研究,目前仍在探索阶段;同样的,西方虽很早已将中国作为一个值得重视的区域并构建起较为完备的研究体系,但无论是早期的“汉学”(Sinology)还是后建立的“中国学”(Chinese Studies),对于中国古典文献的研究虽有一定的积累,但仍处在较为初步的阶段。这种初步阶段的一个明显表现就是双方还未形成一个较为通行的“文献学”及其相关术语的对应译名,术语对应译名的混乱所反映的深层次问题,是双方对于彼此“文献学”及相关领域的内容还相当陌生。虽然学术界新概念、新方法、新名词层出不穷,学术范式也在以较快的速度更新换代,但是在以上所提及的这些基本问题没有得到澄清的情况之下,双方的学术交流可能还只停留在比较浅的层次。
本文以中国的文献学研究为基准,对西方——主要是英文世界——关于文献、文本与书籍史的多种研究路径进行宏观性的介绍,并将其与中国相应研究领域进行对比,以求得出对于双方相关领域的准确理解,从而为双方更深层次的理解与更进一步的学术交流扫清障碍。一、从“文献学”的英译讲起
毛瑞芳曾将“历史文献学”英译为“historical
literature”,她得到此译名的方法,主要是对“历史文献学”这一术语中的各个语素进行了分析。首先,她指出“文献”应该是包含所有文字记载的、内涵较广的一个概念,而英文中literature一词较之于document、text、archive、book、classic等词含义更为广泛,因此“'文献’一词选择literature较为合适,即'所有文字记载’。Literature强调整体性,因此,无论是'官方的、纪实性的文件’、'文献文本’、'历史档案’、'文学文献’,还是'书’,都是'文献’的组成部分,都可以被这个词涵盖。'文献学’也可以用这个词来表达,一是因为literature是一个不可数名词,不适合在词尾加-s变复数,因此,也就不能像西方古典学的名称由'古典’classic变成classics来表达;二是因为'中国历史文献学’名称本身较长,再加the study of来限定,名称会更加冗长,所以简洁明了的表达更上口”。然后,她称“历史文献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历史文献学’指研究1911年前古文献及古文献工作的学问,以时间为限,和其相对的是'新文献学’;而狭义的'历史文献学’则是指研究历史类文献及文献工作的学问,以文献内容为限,和其相对的是其他类别的文献学,如古典文献学等”。而这两种含义都可以用historical这一词表示,因此“历史文献学”就可以译为“historical literature”[1]。
这种使用汉语的思维,以语素对应的方式来翻译术语的译法,会产生很多问题。“literature”一词目前在英语学术界有固定的意义,对应于汉语中的“文学”,是一个有着明确研究范围、研究旨趣和学科架构的学术领域;其下有各类子领域,比如“比较文学”(comparative literature)、“美国文学”(American
literature)等;literature又有各类衍生词汇,亦多与文学有关,比如literary theory即汉语中的“文学理论”。因此,“historical literature”这一生造的术语并未显示出“文献学”的专业特性,在英语思维中容易产生误解,一般人不会认为它是“文献学”。毛氏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却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而是提出一个“原则”,她称:“中国历史文献学中有相当一部分词汇是中国文化和学术界独有的,在外语中找不到确切的对应词汇。因此,一味在外语中寻找专业术语相对应的词汇,难免有'都不够贴切’的感觉。显然,采取这种'外语’中心论原则英译专业词汇,会影响专业外语的准确定位和功能性最大发挥。笔者认为英译专业术语更适宜采取中国历史文献学本位论,辅以西方学者的使用习惯和学界的接受程度为参考。在这样的原则指导下, 英译专业术语可以先研讨、制定出本专业中文核心术语表, 再逐个词来考察、创造最终确定其英译。这样形成的专业术语表才更符合本学科的内涵和交流需要。”[2]翻译问题,实则是文化的跨越语言的交流,重要之处在于意义的交流,而其难处就在于两种文化之间有着语言的隔阂。一般情况下,任何两种文化中的概念和语汇都很少有完全严丝合缝的一一对应,所以,翻译交流之时容许有一定的混沌性来消解这种隔阂。举个极端点的例子,英文中的people和汉语中的“人”所指的本不是同一种类的人,但将二者对应,并不阻碍两种文化的交流,只有在特殊情况之下才需要指出,不同文化背景之下的人也许在生理特征、心理特点上略有差别。“在外语中寻找专业术语相对应的词汇”,是翻译工作应该首先考虑的方法。只有使用对于外语方来讲更为明确、直白的称呼,而非以汉语的习惯来生造词汇,才能让交流顺利进行。
术语的翻译,尤其应该以术语本身所包含的整体含义为根本。无论是“文献学”还是“历史文献学”,其本身是一个专业术语,而且是一个学术领域的专名,翻译之时,应该考虑本领域的研究范围、视角、方法、学科构架等等,而不应该根据汉语的习惯拆分其语素,个别翻译,然后粘合。二、文字书写的三个层次与“文本学”
将“文献学”翻译为“literature”,其实是混淆了“文学”与“文献学”之间的区别。一般认为,文学指的是语言、文字的艺术,是使用语言或文字的符号来表达个体主观意愿、情感、认知,并与其他个体或群体进行交流的媒介。广义的文学,其实不仅仅是诗词歌赋、也不仅仅关乎风花雪月,它包含一切通过语言与文字进行表达与交流的行为,相关的研究会包含表达者、表达方式、产生的意义、效果、审美内涵、政治意图、情感力量等等。现代汉语中的“文学”和目前英文中“literature”的核心内涵皆是如此,而这些都不是“文献学”所关注的内容。若以最广义的“文”的意义来看,它可以包括“文献”,在历史上也偶尔指称“文献”,但在现代的学科体系之下,各自的内涵已经非常明确,不容混而言之。
2009年公布的中国国家标准《文献著录总则》(GB/T
3792.1-2009)定义“文献”为“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在当今的技术背景下,这一定义可以作如下理解:首先,文献应当包括传统的文字、图像、符号等内容,也应该包含影像、声音等知识和信息的载体;相应的,文献的载体除了传统的图书之外,还须加入胶片、磁带、光盘、硬盘甚至于网络等等。据此,理想化的“文献学”,应该是以所有知识和信息的载体为研究对象的学术领域。“文献”定义的一个重要概念是“载体”,也就是承载文字、图像、影音资料的实物,以古典文献或历史文献而论,文献学以图书、档案、图画和铭文等的形成、流传、演变、整理与利用为主要研究内容,首要任务是为各类学术研究和文化普及提供可靠的资料基础,它与“文学”在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研究旨趣等方面都截然有别。
所有以文本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问几乎都要先进行“文献学”的相关梳理,“文献学”是其必要的基础,因此,各种文化、语言背景之下的学术,都有“文献学”,它并非中国所独有。今日的西方世界与中国都有非常悠久的学术文化传统,都有自成体系的文献学的发展历史,也产生了各类不同的又互相有所重叠的类似领域。如何确定“文献学”的英文译名,需要先认识西方文献学相关研究的历史,此详下文所述。
由“文学”与“文献学”的区别可以发现,人类所书写和制作的文字、图像、符号等对于研究者来说至少有三个层次:处于最基础的层次者为其载体,处于最上层并直接发生应有的效用者为其所含的内容与意义,而这两个层次之间其实还有一个在传统的理论研究中颇受忽视的层次,那就是文字、图像和符号本身,现代学术统称其为“文本”,英文中有“text”一词与之对应。文本不可能凭空存在,它必然存在于一定的载体之上,载体可以影响文本的色彩、大小、排列方式、呈现样貌等,但同样载体上的文本又有一定的自由度,并非全然决定于载体。文本自己不产生意义,文本意义的产生有赖于阅读与阐释;文本是意义的承载者,不同的文本面貌会影响文本的阅读与接收。文本本身具有的特性,西人称之为“textuality”,即“文本性”;以文本特性本身为研究对象者,可以称为“textual
study”,即“文本学”;与之密切相关者还有近来颇为流行的“hermeneutics”,中译为“阐释学”。文本学与阐释学都是以文本的阅读、解释、影响为中心的学科,与处于更为基础的层次的文献学和处于较高层次的文学、宗教、历史、哲学等等都有关联甚至重叠,对相关学科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从学术领域的角度来讲,毕竟也有着自身较为独特的研究对象、方法和视角。
作为一个独立研究领域的“文本学”发轫于欧美学术界,目前其学科建设已经相对完善,不仅已有多种以“textuality”或者“textual studies”及其相关词汇命名的书籍,从总体上介绍文本学的研究方法与研究实践[3],而且还出现了几个非常重要的分支学科:比如法国学者热奈特(Gérard Genette)提出“副文本”(paratext)的概念,从围绕正文而存在的前言(preface)、后序(epilogue)、致谢(acknowledge)、附录(appendix)、注释(annotation)、题跋(colophon)、书评(review)等文本出发,讨论文本的意义与阐释问题[4];又如西方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起由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福柯(Michel Foucault)等学者提出的“作者问题”(authorship)这一研究路径,主张从文本的作者(包括“作者缺席”,即the absence
of author)的角度讨论文本的本意、使用义、衍生义等问题,对中外文学、史学的研究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5];再如至今仍有兴盛趋势的“符号学”(semiology),受到语言学、人类学与社会学的浸染,试图从一切人类所创造的符号中解读出意义[6]。文本学内各个分支学科互相交融,又与其他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交互影响,成为文史研究中一个体量较为庞大的专业领域,而且其中往往包含校勘学、图书编辑与整理等较为传统的内容,还会涉及文本文化、书写文化等内容,是目前西方学术界一支不容忽视的庞大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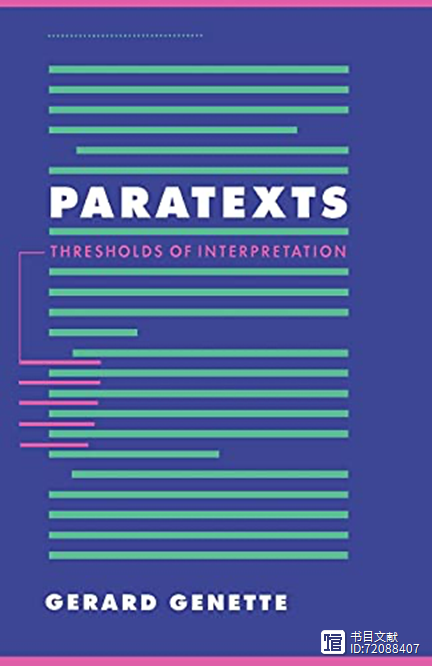
大致来讲,文本学关注各类文本的生产(比如“作者问题”等)、流传与改编(比如改写、转译、副文本问题、跨文化交流等)、解读(比如“符号学”、“阐释学”等)以及不同类型文本的互动等问题,它以认识和解读“文本”(包括所有书写、符号、图像等)为目标,将文本视为人类表达自我的一种方法,通过解读文本背后的含义来理解一个社会的文化以及浸淫于其中的个体。因此,文本学其实已经超越了传统的“文学”研究,而变成一个基础性的研究方法,对所有文史研究皆有弥漫性的影响,其研究领域与文献学有所重叠,但二者毕竟侧重点与研究方法有异。
传统的文学、历史、哲学研究和文献学研究都会涉及文本研究,只是未将其作为一种专门的视角;当今学术界将“文本学”视为一个较为独立的领域,实则是学术研究细化的一个表现,其功过暂不评议,其影响则是木已成舟。三、中国与西方的“文献学”
在中国的现代学术体系之下,研究文献的第一个层次的学术领域是“文献学”,在不同的语境下又可称为“古典文献学”“历史文献学”等。1980年代以来,与文献学有关的通论、概论类书籍已有四十馀种[7],其名或为“文献学”“古典文献学”“古代文献学”“历史文献学”,或作“校雠学”“古籍整理学”等,不一而足;其编排方式或以传统的“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等为核心,辅以“辑佚”“辨伪”“古籍的典藏”“古籍的句读与注释”“古文献学史”“四部典籍的介绍”等内容,或者另立新名,称为文献的“载体、类别和形式”“标点、注释与今译”“编纂与流传”“阅读与检索”“文献学的分支学科”等等。但无论从名目上如何推陈出新,基本方法与内容其实还是“研究文献的形态、文献的整理方法、文献的鉴别、文献的分类与编目、文献的收藏、文献的形成发展的历史、各种文献的特点与用途、文献的检索等等”[8]。其实将上述内容总结起来即可看出,文献学最为重要和基础的内容还是“版本学”“目录学”与“校勘学”。版本学研究文献载体之特征及其产生、流传、演变、鉴别与收藏诸问题,目录学重在考察文献的著录、分类与检索,校勘学则以辨正文本、整理文献为主。这其实是研究任何形式的文本皆要处理的问题,也是西方文献学最为重要和基础的内容,故而西方亦有较为对应的学科——只是由于中西文字、书籍形态等有差异,因此处理的方法也随之有所不同。现对西方的“文献学”进行简单的介绍,并谈一谈中西“文献学”及其内含各个子领域的译名问题。
在英文学术界,与中文“文献学”最接近的领域应该是“bibliography”(亦可写作“bibliology”)。日文将此词译为“书志学”或“图书学”,即记录与研究书籍之学,其范围包括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等一系列以文献载体为中心的内容[9]。日文中又有“文献学”一词,则是以研究文字、语言、古籍训释等为中心,旨在通过研究词汇之意涵来搞清楚经典的意义,类似于中国传统的“小学”以及今日所称的“语文学”,对应于英文中的“philology”,它与以书籍和文献载体为中心的文献学(bibliography)有一定的差别。长泽规矩也《图书学辞典》的“文献学”条即指出:“我国文学界自昭和初年以来,将其与'书志学’视为同义来使用,这是不对的。”[10]
Bibliography长期以来在中文中被译为“目录学”,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英文中bibliography这一领域的成果中体量最大的就是各类书籍的目录,在西方学术界,狭义的bibliography的确也可以指“目录学”,而中国研究者接触最多的资料也是各类目录,因此,大部分中国研究者长期以来误以bibliography为简单的目录,甚至不能深刻理解西人文章后所附“bibliography”(一般译为“参考文献”)的学术意义。中文称“bibliography”为“目录学”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西方书籍的特点与演变史和中国有很大差别,因此西方没有形成如中国“版本学”一类的较为独立的领域,“目录学”显得一家独大,容易给我们造成误解。事实上,bibliography的词根为Byblos(比布鲁斯),是古代腓尼基一个港口,尼罗河三角洲所生产的莎草纸(papyrus)从此港口进入希腊,因此希腊人称莎草纸为byblospaparus,并衍生出biblion和biblia等词,皆指古代的书,基督教经典《圣经》(Bible)之名即源于此。Bibliography的词缀“-graphy”亦起源于古希腊,意为书写和记录,所以bibliography的本意就是记录书籍,有了一定的学术积累之后,即产生“志书之学”或称“记录与研究图书之学”,但要记录古籍,往往先要鉴定、归类甚至整理古籍,因此它有着更广泛的意涵,并非仅仅是编目工作。而中国最早的系统记录书籍的行为一般认为是汉刘向、刘歆父子整理群书并著为目录,传统学者称此为“校雠学”,其实即为今日的文献学,同样并非仅仅是目录学。
西方现代bibliography的建立经过了学者的长期探索,后由Fredson Bowers (1905-1991)整合并为西方学者普遍接受[11]。Bowers称bibliography包含五个主要的内容:
第一是enumerative bibliography(亦可称为compilative bibliography),即图书简目,它是19世纪之前西方书目的主要形式,也是一般理解中“目录”的一般样貌,与一般图书馆的存藏目录(catalogue)意义接近,但enumerative bibliography可作为一个学术领域之指称,被译为“列举目录学”或“列举书志学”,从事者往往会思考目录编制中的原则、其背后的学术因素,也就是说,编目者不是死板地根据既有的规则来填空,而是要主动地思考一个文献与整个文献体系的关系,适当的时候甚至会调整整体目录的结构,以更为准确地反映学术的变迁,此即宋代文献学家郑樵所谓“类例既分,学术自明”[12]。
Bibliography的第二个内容是historical bibliography,其义近似于“文献生产史”。有学者称其为“历史文献学”“历史目录学”,甚至用其作为“史志目录”的译名,皆与其本意不甚相合。关于historical bibliography的研究内容,Bowers称,“我认为,我们应该在其中包含印刷者、造纸者、装订者、排字者、刻字者、出版商、书商,以及其他以任何方式与书籍的生产以及随之而来的流传有关的任何人员的传记和历史的研究。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还应该纳入成本、书价、贩卖与流传方式的研究,印刷品、题跋、版权项和书中广告的研究,将印刷品和其材料作为艺术而进行的所有的美学方面的研究,与文本的物质形态、流传方式有关的创作环境,以及作者与出版的商业程序之间关系的所有考察。”[13]也就是说,historical bibliography要研究书籍生产与流传的历史背景、技术条件和社会结构等内容。其范围接近于“印刷史”和近来颇为流行的“书籍史”,但与之不同的是,Bowers等文献学家所关注的只是“文献生产史”,是一个背景,其目的是为了加深对于图书本身认识的准确性以在著录时做到准确描述,而没有“印刷史”和“书籍史”的问题意识。但无论如何,historical bibliography已经超出了中文“目录学”的范畴,而与“版本学”“印刷史”有更多的重叠。与此情形相类似者还有下一个部分。
Bowers称bibliography的第三个内容是analytical bibliography,较为通行的译名是“分析书志学”,其研究范围与中文语境之下的“版本学”更为接近[14]。分析书志学以实体的书及其形态特征(physical evidence)作为考察的对象,通过分析不同书的字体(排字)、刷印、装订、版面、刊刻过程等来鉴定版本并分析不同版本之间的关系,其核心内容其实类似于中国“版本学”的两个基本任务——进行版本鉴定,考察版本系统。但analytical bibliography却不适宜翻译为“版本学”,主要原因在于中西书籍的基本特征和演变历史具有较大差异,因此各自形成了不同类型的研究书籍物质形态的学问。中国版本学,狭义上来讲,其主要研究对象是古代的刻本,即雕版印刷的古籍,兼及活字印刷的古籍以及印刷术普及之后的稿钞本,也就是说,它处理的是“刻本时代”的文献[15]。中国的刻本时代约始于中唐,下延可至民国时期,前后约有一千年的历史,此一时段所产生的古籍和其他文献从数量上来讲占据了现存古文献的绝大多数,因此有条件,也有必要为其建立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刻本时代之前的纸质写本形成了专门的“写本学”,以金、石、竹、帛等为书写材料的早期文本则因文字古老、材质特殊且书写的性质与后代有异而分别形成了“甲骨学”、“金石学”、
“简帛学”等专门的研究领域,此皆非“版本学”所能涵盖。
在西方,分析书志学是二十世纪初在Alfred W. Pollard、Ronald B. McKerrow、Walter W. Greg等学者研究莎士比亚作品集的各种印本的过程中逐步建立的,它以印刷书为主要研究对象。西方的印刷史迟至十五世纪中期才开始,而且由于西方文字的基本字母数量往往只有几十个,因此便于进行活字印刷,其制字、排版、印刷、销售等程序与中国古代流行的雕版印刷极为不同。大体来讲,西方的机器活字印刷术多为商业行为,是一种以机器生产的方式在大小工场中进行的商业行为,是一种近代化的书籍生产方式。对其书籍的研究,不需要处理中国版本学中初印、后印、翻刻、覆刻、原版、补版、修版、书手、刻工等一系列问题,但需要解决机器的修整、技术的革新、商业运作的结构、印刷商与工人之间的雇佣关系、不同版次的修改调整乃至于版税、审查、赞助人等一系列被归为“印刷史”的问题。在bibliography中,关于印刷史的内容被归入historical bibliography之下,关于印刷书的特征的研究才被归入analytical bibliography之下,有些学者也会取消historical
bibliography这个名目,径以analytical bibliography称呼所有对于印刷书与印刷史的研究。历史学中有科学技术史一门,其中一些学者专门研究印刷术,但历史学家主要关注其中的技术要素,他们要回答的问题是:作为技术的印刷术如何促进社会的变革与历史的进步[16];而在文献学家的眼中,研究analytical bibliography的首要目的是了解书籍文献的演变,其中心是文献。作为独立学科的“分析书志学”与“印刷史”的研究范围多有重叠,但二者的问题意识有本质的区别。简言之,西方印刷术普及较晚,历史较短,且已与近代文明有所牵连,有关印刷史与印刷书的研究,被历史学(印刷史)与书志学(bibliography)所瓜分,并无以讨论版本鉴定和版本系统为主要内容的“版本学”这一独立的学术领域,西方研究版本的学者有时称自己所从事者为“study of book editions”,此可作为中国“版本学”的对应译名,但需注意二者所处理的对象、研究方法等皆有不小的区别。
西方的印刷史出现较晚,但其书写的历史并不比中国短,在印刷时代来临之前(以及印刷术出现后的几个世纪),书籍和文献皆以“写本”(manuscript)的形式流行。因此,西方“写本学”这一领域体量极为庞大,在现代学术体系中,西人称写本学为“manuscript studies”,此与中国的“写本学”基本上可以一一对应,而且与中国情形相似,西方也有古写本和中世纪(中古)写本之区别。西人称研究中世纪之前的早期书写、铭文、古文字的专业领域为“paleography”,这个术语的词根来自于希腊文palaios,意指远古的东西,加上词缀-graphy(书写),意即“古文书学”。在西方学者眼中,中国的“甲骨学”、“金石学”、“简帛学”等皆可归入“古文书学”之中,且中西从事古文书学的很多学者都是考古学家。在“写本学”(manuscript studies)的研究中,占据主要地位者是研究中世纪的写本文献。欧洲中世纪写本与中国中古写本有很大的区别,仅从书写材料和书籍形制上来讲,中国中古写本多为书写在纸上的卷子,形制类似于古希腊罗马时期和中世纪早期流行的scroll(莎草纸卷或者羊皮卷),而西方从三世纪开始,卷子逐渐式微,而用兽皮纸(parchment)所做的册子本(codex)快速兴起并成为西方中世纪书籍文献的主要形制,专门研究中世纪写本册子遂成为一个体量不小的专门学科,西人称之为codicology,目前也多被译为“写本学”,只不过其内涵要比“manuscript studies”小一些[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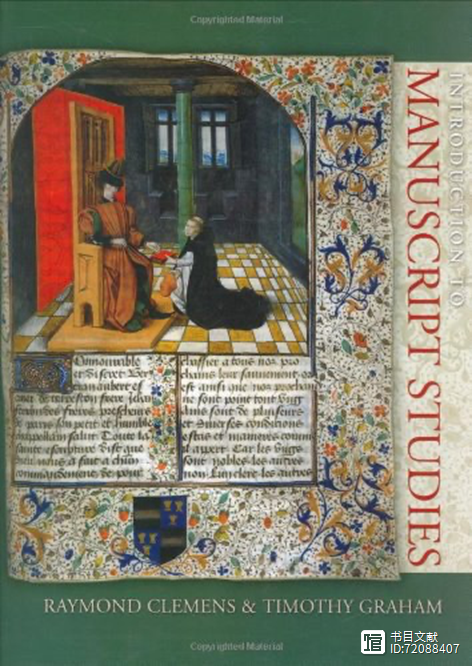
Bibliography的第四个内容是descriptive bibliography,可译为“描述书志学”,其成果的呈现形式类似于中国的提要目录,即尽可能多地收集与一部书的物质形态有关的信息——通常要借助前三个内容,特别是分析书志学的研究成果——详列各个版本,比较分析,以得到此书尽可能准确而全面的信息,并将其记录下来。描述型书志,实则记载的是每一部书籍的历史,是“a genre of historical writing”(一种历史书写的体裁)[18]。上文已经提到,bibliography的本意是记录书籍,enumerative bibliography与descriptive bibliography最为符合bibliography的原始意涵,同时,这两类bibliography亦与中国“目录学”这一领域颇为类似,故而一些中国学者将bibliography作为“目录学”的对应译名并非完全错误,只是需要明确,此仅取bibliography的狭义内涵。
Bibliography的第五个内容为textual bibliography,即“文本书志学”[19],用书籍的文本特征来确定同一书籍不同版本之间的关系。此与“校勘学”,即“textual criticism”关系尤近[20]。但根据Bowers等人的界定,校勘学是要确定一个正确的、符合作者“原意”的文本,即首先借助bibliography的各种手段找到一书的所有版本,经过比对找出异文,通过考辨确定孰是孰非,最后整理(edit)文本以得到一个“原本”或“真本”(authentic text);而textual bibliography的目的其实是用校勘学来确定不同版本之间的关系,不关心内容正确与否,只关心各个异文之间的关系,并以此来确定版本之间的关系[21]。然而,Bowers对二者的这种区别并未被学术界普遍接受,一般学者还是将校勘学整体纳入bibliography的范围之内,比如,在西方目前较为流行的一本书籍史研究通论性著作A Compan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Book(《书籍史手册》)中,讨论“Textual Bibliography”的那一小节也包括了textual criticism的发展历史与研究现状[22]。
校勘学旨在整理(edit)先前的文献,使其便于阅读,整理古籍是现代文献学的一个基本的任务。而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皆有非常悠久的整理古籍的传统。西方早在古希腊晚期(大约公元前3世纪到2世纪)就有了对古希腊经典与《圣经》早期文本的研究与整理,其研究表现在对于经典文本的评注与阐释,并形成了最早的经典注释,西人称之为“scholia”,而其整理,即对于文本错误的改正、文本顺序的调整以及对于伪造文本的辨别与剔除等等,则是最早的校勘实践。之后,书籍渐多,校勘学也缓慢发展。“文艺复兴”之后,在研究整理古希腊罗马经典与莎士比亚等人通俗文本的基础之上,西方的校勘学理论逐渐完备,并出现了如Richard Bentley(1662-1742)、Jeremiah Markland (1693-1776)、Karl Lachmann(1793-1853)、Alfred Edward Housman(1859-1936)、Joseph Bédier(1864-1938)等伟大的校勘学家。校勘学以整理文本为第一要务,而整理文本则需要版本、目录学的知识,因此古代的校勘学家同时也都是版本目录学家,此在二十世纪以后的校勘学中有更为明显的表现。进入二十世纪以后,Ronald B. McKerrow(1872-1940)、Walter W. Greg(1875-1959)、Bowers与G. Thomas Tanselle(1934-)等学者将校勘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层次,他们更重视文本的更早版本,希望以此恢复作者所写的“原本”,进而探寻作者的“原意”(authorial intention)。显然,要从事此类研究,必须要对古籍的目录与版本有深入的了解。这一批校勘学家所从事的研究在西方学界被称为“new bibliography”,即在现代学者的认识之中,textual criticism已经成为bibliography的一个子领域[23]。单从校勘学这一小领域来说,1970年代以来,J. McGann与D.
F. McKenzie等学者开始检讨“new bibliography”对于书籍原本与作者原意的执迷,提出每一个文本皆是作者、编者以及所有参与文本流传的人的共同创作,每一个文本皆在其历史时期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因此应该研究“文本的社会学”(sociology of the texts)[24]。此则受到了社会学、人类学与文化史的影响,与“书籍史”殊途同归。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西方bibliography的核心内容类似于中国传统的版本目录之学,旁及校勘学以及出版史、印刷史等内容,基本上可以对应于中国的文献学。西方人一般称与书籍(特别是古籍)的版本、目录等有关的文献学研究为“bibliographic studies”,可见此一概念在西方学术界的一般意义。
需要指出的是,Sheldon Pollock等一批学者将校勘学(textual criticism)归入philology,而且几乎将所有与书籍研究、文本研究、注解、阐释、文字、音韵,乃至于历史语言学(historical linguistics)等有关者皆归入“philology”这一领域中[25],使其研究范围与文献学或bibliography有很大的重合。然而,在一般学者眼中,philology(语文学)还是以传统的语言、文字、语音和校勘学研究为主体,版本目录学等内容只是其辅助内容,Sheldon Pollock 等人的观点并未得到普遍接受。在目前中国的文献学界,古文献的整理以及与古文献整理直接相关的研究一直占有最为重要的地位,因此,除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之外,文字学、音韵学和训诂学等传统称为“小学”的内容也是文献学家研究的重点,某些古籍整理研究单位对于小学的研究、对于小学类文献的整理以及对于辞书的编纂甚至是其工作的主要内容,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很多古籍整理研究单位也将“文献学”翻译为“philology”,这其实是持有与Sheldon Pollock等欧美学者相同的观念:认为“philology”、“语文学”或“小学”才应是古典文本研究的核心内容。基于此,笔者以为,在多数情境下可以将“文献学”英译为“bibliography and philology”,此一译名不仅包含更广,且不失准确,更符合当前我国文献学领域的实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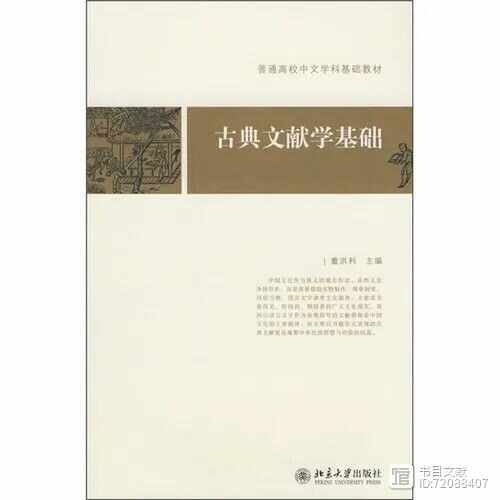
四、书籍史转向
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传统文献学(bibliography and philology)的工作重点皆是整理古籍、编制目录、纂辑辞书,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的基础性工作,因此很多现代学者将其视为工具性的学科,极端一点的甚至认为文献学家只会钻营故纸堆而缺乏问题意识,只能依附于某一确定的文史研究领域而没有形成独立学科的必要。在这样的处境之下,很多文献学家开始思考如何构建一个以书籍和文献为中心而具有更广阔的研究视野和更明确的问题意识的现代学科。这种寻求突破或者转向的尝试,最早由西方的文献学家开始进行,而促成此一转向的重要动因,则是20世纪中期开始在西方学界兴起的“书籍史”。
书籍史(history of
the book)是20世纪50年代末期由法国年鉴学派建立起来的新领域,它深受社会史、文化史、人类学等学科的影响,“用社会史和文化史的方法研究人类如何沟通和交流”,借以理解“人们的想法和观念是怎样通过印刷品得到传播的”,以及“阅读又是怎样反过来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26]。换句话说,西方的书籍史研究者最初多是历史学出身,因此他们关注书籍的生产、流转与阅读,本是为了回答书籍如何塑造社会与文化这一基本的历史问题。比如,目前美国书史研究的执牛耳者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原是法国大革命史研究的专家,他进入书籍史领域,是因看到文化与知识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在塑造大众观念、乃至改变社会方面发挥了非常基础的作用,达恩顿投入了巨大的精力研究法国大革命前后的文化生产、知识流转及其社会影响,成为历史研究的一个足资借鉴的典型[27]。他除了是一位书籍史家之外,通常还被称为思想文化史研究的学者,是思想史和文化史领域新研究范式的建立者。这样的由书籍而达于思想文化史的研究,从史学上来讲,是一个首尾完备的研究样态,它不仅可以提供很多方法论上的启示,而且道出书籍与文献研究所能解决的问题,包括史学上的、文化学上的和社会学上的多种多样的可能性。也就是说,研究者可以从这些思想史、文化史研究中汲取问题意识。
其实历史学中以书籍为中心者,还有“出版史”(publishing
history)、“印刷史”(printing history),其研究者多数是社会史家或科技史家。这些历史学家一般将印刷术的发明和变革与其他的技术革新等量齐观,而且多数都持有或重或轻的“技术决定论”观念。比如美国学者伊丽莎白·爱森斯坦(Elizabeth Eisenstein)撰有《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早期近代欧洲的传播与文化变革》(初版于1979年)这一鸿篇巨著,认为欧洲十五世纪中期出现的印刷术所带来的书籍、知识生产与传播的便利,对欧洲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乃至近代革命皆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也就是,从某个角度来讲,是印刷术使得西方进入近代文明[28]。需要指出的是,本书具有非常浓重的西方中心主义与技术决定论的观念。而此种研究路径并非爱森斯坦独有,而是在整个历史学界都有重要的影响。在中国印刷史和出版史方面,较早的专家有美国学者卡特(Thomas Francis Carter),后又有钱存训、张秀民、潘吉星等,皆更看重造纸、制墨、印刷术等技术革新,解决了很多关于古代书籍与文献生产方面的问题,但这些学者本身多有更远的学术追求,即回答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因。这些学者所持的史观往往与“书籍史”研究者略有不同,而且一般是后者批判的靶子。但在“书籍史”以及近年来文化相对主义、后殖民主义和后现代史学等观念和思想流行之后,此类研究也逐渐转向,成为了“印刷文化”(print culture),全然被“书籍史”所包含。
书籍史对文献学的影响也非常大。最著名例子就是英国学者麦肯锡(Donald Francis McKenzie,1931-1999)所提出的“文本的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texts)。麦肯锡曾在剑桥大学学习,后来成为牛津大学目录学与校勘学方面的教授。他曾花费巨大气力阅读了剑桥大学出版社的各类档案,考辨其出版目录,考察其书籍贸易,写下《剑桥大学出版社1696-1712:一个文献学的研究》(Th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691-1712:A
Bibliographic Study)一书;又曾编过英国剧作家威廉·康格里夫的全集(The Complete Works of William Congreve),并写过一系列较为传统的文献学研究著作,是一位优秀的文献学家。进入1980年代以后,在书籍史和新的文本批评理论的影响下,麦肯锡尝试向书籍史方向靠拢,他著有《文献学与文本的社会学》(Bibliography and the
Sociology of Texts,初版于1989年)一书,讨论文本物质层面的要素如何影响文本的传播和接受等内容,书中有大量内容讨论书籍的各类版本之增演与递变及其对文本意义产生的影响,从中可以看出作者具有深厚的文献学(主要为版本学和校勘学)修养,但作者落脚于文本的各类变形对于读者的影响,尝试从文本的形式中追寻各种或隐或显的意义,这种对于意义与功能的追寻,则具有明显的社会史、文化史的意味。这是麦肯锡有意为之的结果。书中,麦肯锡称自己所从事者为新的“文献学”,称其“是一门研究作为一种记录方式的文本,及其生产、传播和接受过程的学科”,它“研究作家、印刷工和出版商对于文本的创作、版面设计以及传播;研究文本通过由批发商、零售商和教师组成的团体的配销过程;研究图书馆员的收藏和分类;它们对于读者的意义……以及读者对于它们的富有创造力的改编”[29]。麦肯锡的研究展现了一个文献学家对于旧有范式突破的尝试,这也表明西方文献学向书籍史转向的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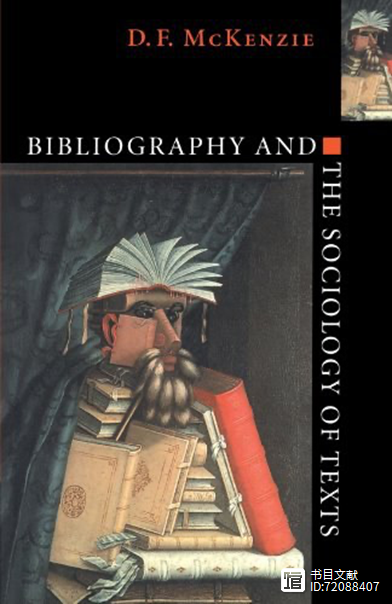
西方书籍史的影响很早就波及到了海内外对于中国古代书籍、文献的研究中,而且近三四十年间已经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成绩。但无论是西方的汉学家还是中国本土的学者,对于“书籍史”这一新路径最为敏感的,还是历史学家以及部分文学研究者[30],文献学家则迟至近几年才开始对其略有涉足。南京大学文学院赵益教授撰有《从文献史、书籍史到文献文化史》一文,最早明确提出中国的文献学当向西方书籍史借鉴,但赵文反对直接照搬西方理论,而强调中国的文献学家更应该“在借鉴西方书籍史观照视野的过程中……充分反思研究对象——中国古代文献、书籍——的客观属性”,从而提出适合于中国古代书籍与文献研究的新问题,他将这种研究命名为“文献文化史”[31]。“文献文化史”是中国本土学者基于中国自有的“文献学”所开创的新领域,虽对西方学术有所借鉴,但立足于中国本位,并期望找到不同于西方的——或者更准确的说,找出更贴近中国历史事实的——问题意识,从而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束缚,取得对于自身历史与文化的准确理解。而且,在很多研究者的观念之中,书籍的社会史、文化史或者文献文化史等并不能替代版本学、目录学等传统文献学基础内容,而仅可作为其研究领域之拓展。总之,中国书籍史这一领域尚处在草创阶段,是否会有所成就,还有待于时间的检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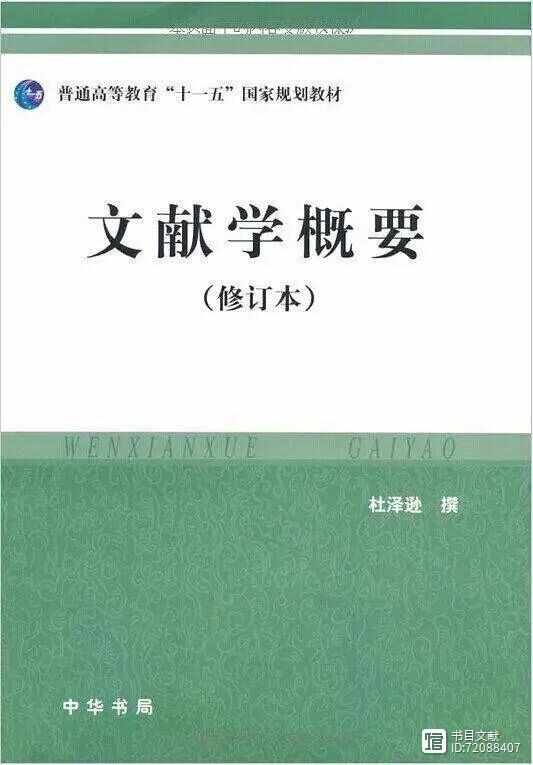
五、结语
语言、符号、文字与图像的产生,原是为了交流信息和记录思想,积累渐多,则成为文化与思想的载体,最早的“学术”应该是为了认识并传承这些口头的和视觉的“文本”,并以其中所蕴含的思想与文化来指导对于宇宙人生的理解和探索,学术处于混沌一元的状态,后来,如《庄子·天下篇》所云,道术为天下裂,方产生了对于各类不同文本的研究。在此过程中,由于言语易逝,而图像与特殊符号难解,记录语言的文字文本保存渐多,成为后世学术的主要内容,这是文献学得以成立的条件和基础。
中国与西方都有极为悠久的文献学传统,既然皆为研究“文献”之学,二者在基本的学术任务、研究方法、分支领域等方面皆有极大的相似之处;但由于各自的历史以及文献本身的不同性格,各自在学科体系、发展程度、内部构架及其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上又有较大的差别,这些差别则可能是导致中西学术研究乃至于思维方式相异的一个重要原因。
学术上的中西对比,一般会有“求同”与“辨异”两个途径和目标。本文主要对二十世纪以来中国与英语世界的文献学进行了宏观的对比,且以“求同”为标的,梳理了中西文献学在学科构成、发展规律与风格特征等方面的相似之处,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文献学”及其相关术语的相对更为合适的英文译名。这样做的目的,并非刻意与前贤较是非,而是希望通过中西对比来促成东西对话,从更为广阔的视野上来理解作为独立学术领域的文献学,进而为能够更为准确地理解作为“他者”的西方建立一个理论平台。举例而言,只有知晓中国与西方皆有处理文本是非问题的校勘学(textual criticism),并懂得其在文史研究中所起的作用和所处的地位,才能理解过往的学者为何会在这项工作中投注如此多的精力以及他们所做的工作为何会有诸般差异。具体而言,目前中国校勘学的理论是建立在以刻本校勘为主的前提上的,以版本比对(也就是一般所说的“对校”)为主要方法,通过考据分析来辨别异文优劣,再去伪存真,获得定本。而二十世纪初数量巨大的敦煌写卷出土之后,面对写本的复杂状况,校勘学界至今也未建立一个完善的进行写本校勘、写刻对勘的基本方法。与之相反,西方本有历时弥久的写本传统,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的写本校勘经验,同时也有大量的理论探讨,而因其印刷术发明较晚,版本校勘方面则稍显薄弱。通过探析中西传统校勘学皆以确定真本为主要任务,即可知双方的学术有着类似的基础和方法;通过对比二者风格之差异,即有可能互相学习,深入交流,共同促进。
若将中西文献学的发展史作为一种学术史来看待,本文的讨论只是初步的尝试,还有很多更为细致的“辨异”的问题需要解决,比如:中国与西方的铭文系统有哪些结构性的(非语言文字性的)差异,如何理解这些差异,它们对于早期中西思想与文化分别有哪些影响?西方的写本与中国的写本在哪些方面有比较重要的异同,导致的研究历史、研究方法和理论有哪些差异,中国如何借鉴西方写本学来展开自己的写本研究?中国的雕版印刷传统和西方的活字印刷传统各有什么特点,如何在历史中发挥了哪些作用,两个体系之间何时、以何种方式开始对话,产生了哪些影响?中西文献学在学科理论、历史、分支领域等方面有哪些系统的差别,这些差别是如何产生的,对于各自的文史研究有哪些影响,如何互相借鉴并改善?西方何以产生了书籍史,今日如何将书籍史的研究方法引入中国古代文献学的研究中去?如何在借鉴西方书籍史方法的同时坚守中国本位的问题意识?除此之外,还有数量更多比这些问题更为微观和具体的问题,这些问题目前已经得到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讨论,但仍处在起步阶段。希望文献学界更多的学者可以扩大视野,在反思中西文献学、文本学与书籍史的基础上形成中国文献学界自己的问题意识,使我国的文献学研究步入新的阶段。注释:[1]毛瑞芳:《中国历史文献学英译名称探研》,《历史文献研究》总第29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96-297页。[2]毛瑞芳:《中国历史文献学英译名称探研》,第297-298页。
[3]较为基础和著名者有Hugh J. Silverman所著Textualities: Between Hermeneutics and
Deconstruction (Routledge, 1994)、Francois Rastier所著Meaning and Textuality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7)、Philip G
Cohen所著Texts and Textuality: Textual
Instability, Theory, and Interpretation (Garland Pub., 1997)、Peter L.
Shillingsburg所著Textuality and Knowledge: Essays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17)、Wesley A.Kort所著Textuality,
Culture and Scripture: A Study in Interrelations(Anthem Press, 2019)等。
[4]热奈特“副文本”理论主要见于热氏两书,其一为 Paratexts: Thresholds of Interpretation (Translated by Jane E.
Lewi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其二为Palimpsests:
Literature in the Second Degree (Translated by Channa Newman and Claude
Doubinsky.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97).
[5] 有关“作者问题”,可参看Roland
Barthes, “The Death of the Author,” in Image
Music Text, trans. and ed. Stephen Heath, Fontana
Press, 1977, pp. 142-148(罗兰·巴特:《作者的死亡》,中译本见巴特著,怀宇译:《罗兰·巴特随笔选》,百花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300-307页);Michel
Foucault, “What is an Author?” in Aesthetics,
Method, and Epistemology, trans. Josue V. Harari, ed. James D. Faubion, The
New Press, 1998, pp. 205-222; Roger Chartier, “Figures of the Author,” in The Order of Books: Readers, Authors, and
Libraries in Europe Between the 14th and 18th Centurie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25-59(罗杰·夏蒂埃:《作者的角色》,中文本见夏蒂埃著,吴泓缈、张璐译:《书籍的秩序:14至18世纪的书写文化与社会》,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29-50页)。
[6]有关符号学的基础性著作,可参看Charles Sanders Peirce, Peirce:
On Signs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1); James Jacób Liszka,A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the Semiotic of
Charles Sanders Peirce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6, 以上两书的中译本合见赵星植编译:《皮尔斯:论符号》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年); Roland
Barthes, Mythologies: Essais (Hill
and Wang, 2012, 中译本为罗兰·巴特著,屠友祥译:《神话修辞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 Barthes, “Éléments de sémiologie” (Communications,
vol. 4.1 [1964], pp. 91-135,中译本为罗兰·巴特著,李幼蒸译:《符号学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 Erwin Panofsky and Gerda
S. Panofsky, Studies in Iconology:
Humanistic Themes in the Art of Renaissance (West view Press,1972); 赵毅衡:《符号学》(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等。
[7]董洪利主编《古典文献学基础》中有“现行文献学著述一览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4页),列有文献学通论与教材类著述32种,此书之后又有多种新著出版,总体数量超过40种。
[8]杜泽逊:《文献学概要(修订本)》,中华书局,2016年,第4页。
[9]参见范凡:《从目录学到书志学——20世纪前期目录学在日本的研究与发展》,《中国图书馆学报》2016年第6期,第117-129页。需要稍作说明的是,“书志学”一词主要是日本图书馆学界和国文学界在使用,日本汉文学界使用较少。
[10]長沢規矩也:《図書学辞典》,三省堂,1979,第3页。
[11]关于Fredson Bowers的生平与学术,参见G. Thomas Tanselle,The Life and Work of Fredson Bowers,
Bibliographical Society of th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1993.以下对于Bowers文献学思想的讨论,主要参考Fredson
Bowers, The Principles of Bibliographical
Descrip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9; Fredson
Bowers,“Bibliography, Pure Bibliography, and Literary Studies,” in David
Finkelstein and Alistair McCleery eds., The
Book History Reader,second edition, Routledge, 2006, pp. 27-34. 关于西方bibliography这一领域的基本状况,还可参考R.
Stokes, The function of bibliography, second edition, Gower, 1982; R. B. Harmon, Elements
of bibliography: A simplified approach, Revised edition. The Scarecrow
Press, 1989; W. P.Williams and C. S. Abbott, An introduction to
bibliographical and textual studies, third edition,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1999.
[12]郑樵:《通志二十略》,中华书局,1995年,第1806页。
[13]Bowers, “Bibliography, Pure Bibliography,
and Literary Studies,” p. 28.
[14]参阅托马斯·坦瑟勒(G. Thomas Tanselle)著,苏杰译:《分析书志学纲要》,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
[15]本文所称“版本”与“版本学”,皆取其狭义内涵,不包含印刷时代之前的写本与简帛文书等。
[16]西方历史学家普遍认为印刷术给西方社会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是西方步入近代文明的一个重要因素,称其为“Gutenberg
Revolution”(古登堡革命),相关讨论参见Elizabeth L. Eisenstein, The Printing Press as an Agent of Change: Communications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s in Early-Modern Europ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本书有作者简写本The Printing Revolution in Early Modern
Europ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Marshall McLuhan, The Gutenberg Galaxy: The Making of
Typographic Man,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62; G. Bechtel, Gutenberg et L’invention de L’imprimerie, Fayard, 1992; A. Kapr, Johann Gutenberg: The Man and his Invention, trans. D. Martin.
Scolar, 1996。
[17]关于manuscript studies的基本情况,参看M. P. Brown, A Guide to Western Historical Scripts from
Antiquity to 1600, British Library,1990; Raymond Clemens and Timothy
Graham,Introduction to Manuscript Studies,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7。关于古代两河流域的泥板书以及古埃及、希腊和罗马的莎草纸文书,参见C. B. F. Walker, Cuneiform, British Museum Press, 1987;
O. Pedersén,Archives and Libraries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CDL Press, 1998; M. Brosius, ed. Ancient Archives and Archival Traditions: Concepts of Record-keeping in
the Ancient Worl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Jaroslav Cerny, Paper and Books in Ancient Egypt, H. K.
Lewis, 1952; Naphtali Lewis, Papyrus in
Classical Antiquity, Clarendon Press, 1974; Eric G. Turner, Greek Manuscripts of the Ancient World, second
edition, Institute of Classical Studies, 1987。欲了解codex的基本情况,可参看Eric G. Turner, The Typology of the Early Codex,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77; B. A. Shailor, The Medieval Book,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88;
Colin H. Roberts and T. C. Skeat,The
Birth of the Codex,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C. de Hamel, A History of Illuminated Manuscripts,
Phaido, 1986; J. G. Alexander, Medieval
Illuminators and their Methods of Work,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2。
[18]G. Thomas Tanselle, “A Description of
Descriptive Bibliography,” Studies in
Bibliography, vol. 45 (1992), p.25.
[19]Bowers指出textual bibliography又可被称为“critical bibliography”(见“Bibliography,
Pure Bibliography, and Literary Studies,” p. 29),而西方一些文献学家称critical bibliography与analytical
bibliography同义。此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故从略。本文仅用“textual bibliography”这一名称。
[20]有学者将“校勘学”翻译为“study of collation”,这样的术语在英文中并不存在,而且稍显诘屈,不可取。
[21]Bowers, “Some Relations of Bibliography to
Editorial Problems,” Studies in
Bibliography, vol. 3 (1950), p. 37.
[22]T. H. Howard-Hill, “Why Bibliography
Matters,” Simon Eliot and Jonathan Rose, eds., A Compan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Book, Wiley-Blackwell, 2009, p.
15.
[23]关于西方校勘学的发展历程,参见Marcus Walsh, “Theories of
Text, Editorial Theory, and Textual Criticism,” in M. Suarez and H. Woudhuysen,
eds.,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the Boo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156-163; J. McGann, A Critique of Modern Textual Criticism,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3; 豪斯曼等著,苏杰编译:《西方校勘学论著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24]McGann, A
Critique of Modern Textual Criticism; D. F. McKenzie, Bibliography and the Sociology of Texts, British Library, 1986.
[25]Sheldon Pollock, Benjamin Elman, Ku-ming
Kevin Chang, eds, World Philolog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26]罗伯特·达恩顿:《书籍史话》,达恩顿著,萧知纬译:《拉莫莱特之吻:有关文化史的思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85-86页。关于西方书籍史的基本情况,除可参看达恩顿的相关著作之外,还可参考彼得·伯克著,刘永华译:《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1929-1989》,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林·亨特编,江政宽译:《新文化史》,麦田出版社,2002年;罗杰·夏蒂埃著,吴泓渺、张璐译:《书籍的秩序:14至18世纪的书写文化与社会》,商务印书馆,2013年。
[27]达恩顿的代表性著作还有《屠猫狂欢:法国文化史钩沉》(吕建忠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法国大革命前的畅销禁书》(郑国强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启蒙运动的生意》(顾杭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旧制度时期的地下文学》(刘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等。
[28]伊丽莎白·爱森斯坦著,何道宽译:《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早期近代欧洲的传播与文化变革》,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29]Donald Francis McKenzie, Bibliography and the Sociology of Text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12-15.
[30]比如中国书籍史研究专家或者涉足书籍史研究者之中,欧美学者如包筠雅(Cynthia J.
Brokaw)、周绍明(J.P. McDermott)、周启荣等,皆为社会史家;美国华裔学者何予明、日本学者大木康等则本属于文学、文化研究者;中国学者如张仲民、曹南屏等,则又多以思想史或文化史研究专长,也是较多出身于史学。关于中国书籍史的研究,可参阅Cynthia
Brokaw,“On the History of the Book in China,”in Cynthia Brokaw and Kai-wing Chow,
eds., Printing and Book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5; 梅尔清撰,刘宗灵等译:《印刷的世界:书籍、出版文化和中华帝国晚期的社会》,《史林》2008 年第4 期;涂丰恩:《明清书籍史的研究回顾》,《新史学》2009
年3月第20卷第1期。
[31]赵益:《从文献史、书籍史到文献文化史》,《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第110-121页。【作者简介】
韦胤宗,博士,武汉大学文学院古籍整理研究所特聘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典文献学与中国书籍史。
相关链接:
韦胤宗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藏《五律英华》薛雪批校辑考
韦胤宗丨图书馆、藏书家与批校本 ——以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所藏中文古籍批校本为中心
韋胤宗丨從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後漢書》過錄何焯批校本看 何焯的史學與校勘學
韋胤宗|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亞洲圖書館藏《九州分野輿圖古今人物事跡》
“书目文献”约稿:凡已经公开发表有关文献学、古代文史相关文章,古籍新书介绍、文史期刊目录摘要等均可。来稿敬请编辑为word格式,可以以文件夹压缩方式配图(含个人介绍),发到邮箱njt724@163.com。感谢您的支持!
- 0000
- 0000
- 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