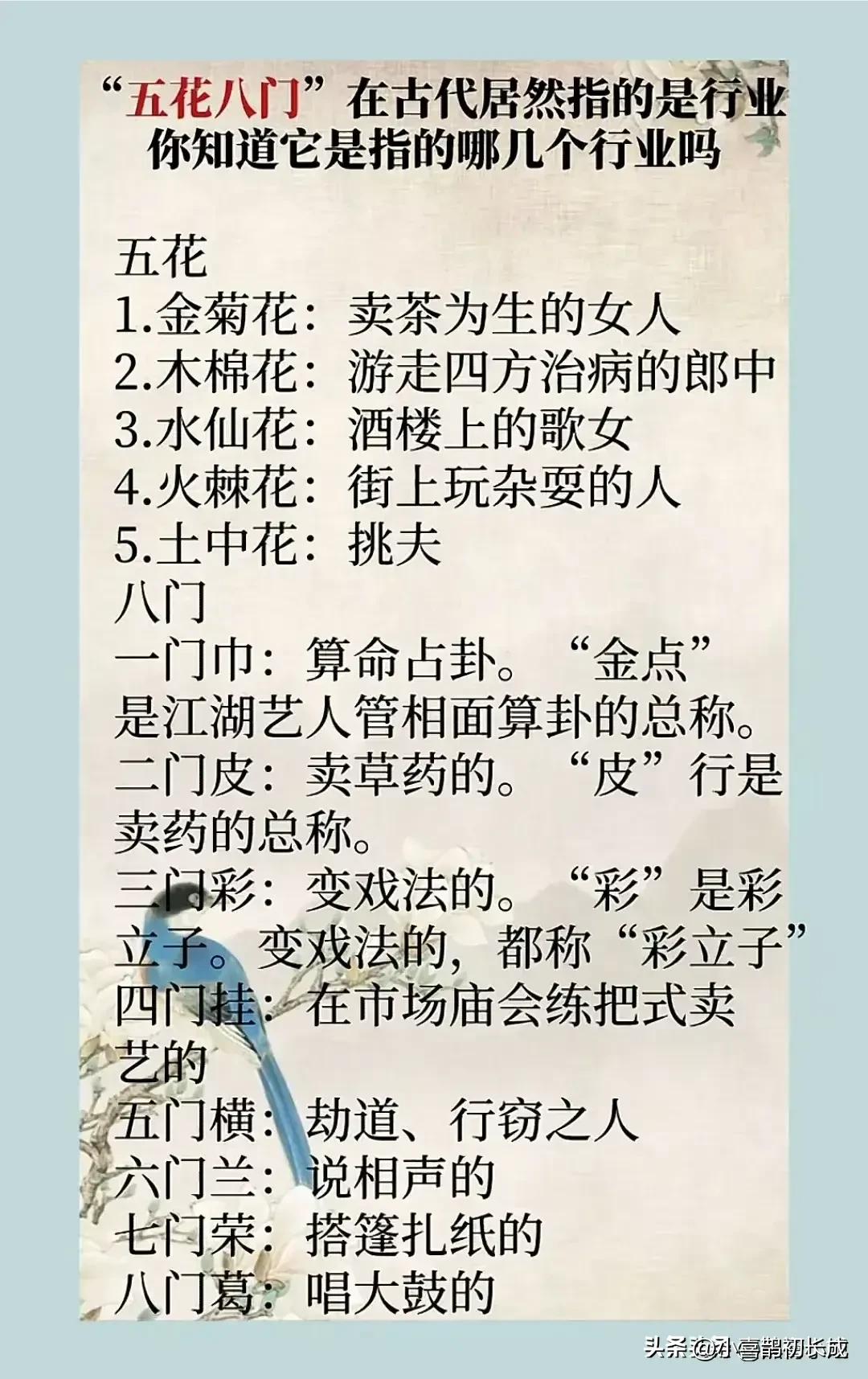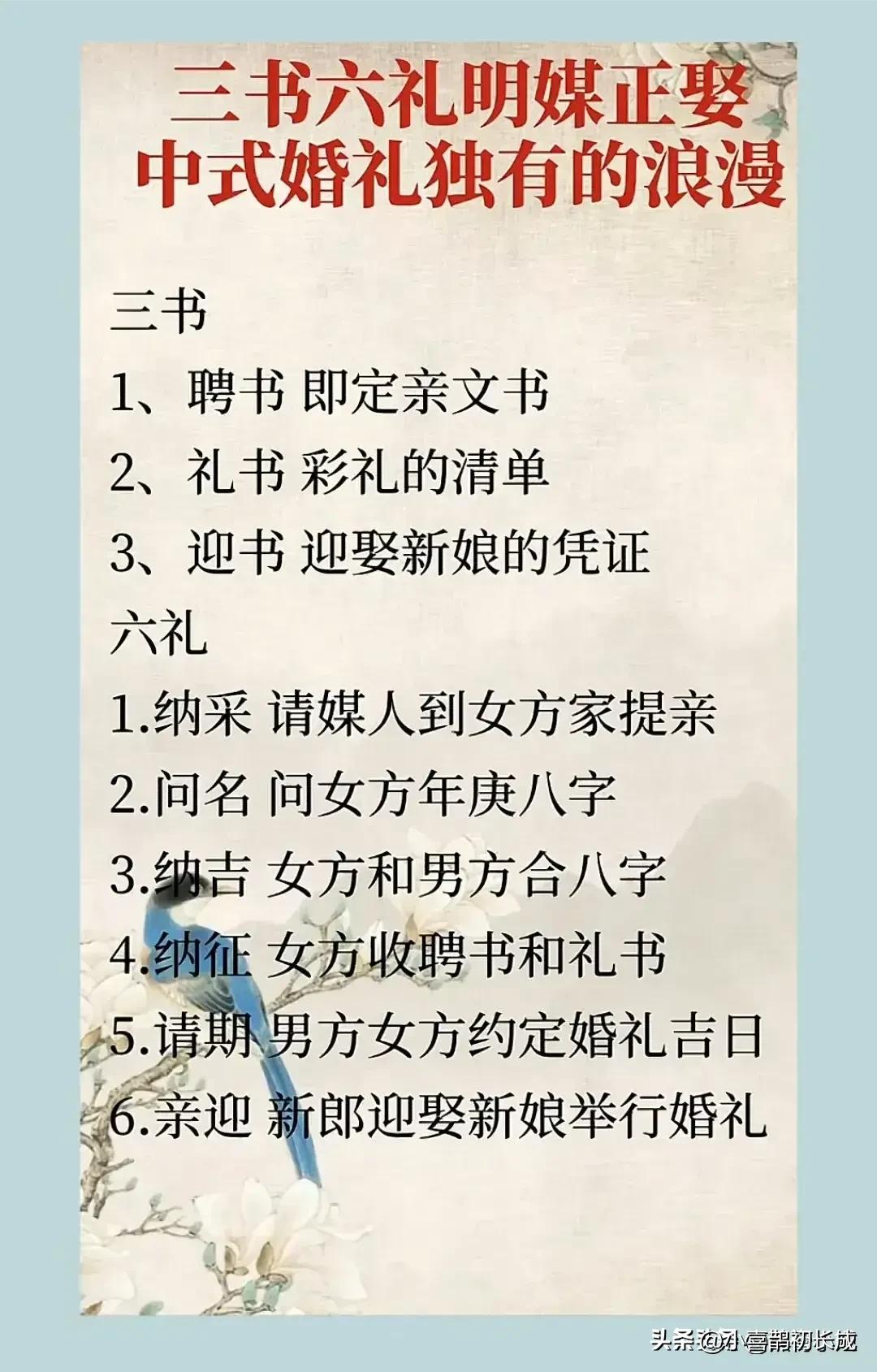凤凰与凤凰
凤凰是一座城的名字,也是一个女子的名字。
我初见此城时,它清凛凛,罩在一片细雨里,吊脚楼的倒影向河心微微撼动,楼上有苗家女子,着绣花的蓝袍、宽脚裤,头上挽一只髻,拿一根银钗儿松松绾着。
我初见此女子,她侧对我坐着,背后是楼顶平台的万丈灯火,映衬着她肌肤如玉,与掩不住的优雅风情,我与她座对多久,便痴怔多久,心里叹着:如此人物。
这城与这女子,除了名字一样之外,我竟找不出刻意的相似处。只这两个,都是独一处地教人欢喜赞叹。
这个城是有名的,三千年前,它已经憩伏于湘西边境。骧蔸部落的仡熊仡夷和廪君蛮巴的后裔在这里刀耕火种,男子将三丈六尺的头帕层层包紧,凶悍地擦拭雪亮的弯刀,女子将四棱突起的银项圈压在颈上,青色宽脚裤边细细地绣出交相缠绕的花枝……何等令人向往。
许多年后这个风情小镇里走出了一个少年,他14岁当兵,20余岁在北京饥寒交迫地写文章。他于86岁高龄上逝世以后,许多人说:“沈从文是一个伟大的作家。”之后便有许多人为他的《边城》所感动,跑到这个小城来看吊脚楼,来看翠翠与傩家老二站立过的地方。
我到凤凰的时侯,刚巧错过了山江三八苗集,因一心要看到实实在在的苗人,遂搭车到苗王府废墟兜转了一圈,那些个斜斜拓开去的石磴木屋,已经好生破败,寨中人大多穿着汉家衣服,升火做饭,闲坐调笑,和一般中原的农村没有什么区别。寨中有老妇人从箱底拿出一套她手绣的衣裳来,宝蓝上衣,靛青大脚裤,袖边、裤边、一件围兜上密密实实是花枝缠绕,这衣服她只在做新嫁娘的时侯穿过,三四十年没上身了。我试穿一回,头上箍了几斤重的包头帕站在灶前装作做饭,四下围看的邻居低声地笑。这倒不知是我来特意看他们的旧风俗呢,还是他们顺路看了我的西洋镜了。
我也在吊脚楼前撑船经过,沱江的水这样浅,看得到水底有绿油油的一片水草在招摇,隔岸桃花正开,桃花下一块孤零零的墓碑,好象没有人看顾的样子,墓上刻的当是“沈-从-文-墓”四字。也去了那条有名的老街。刚好下了小雨,时间又匆促,顺着一地湿搭搭的青石板砖,在各个低矮的屋檐间仓皇地进进出出,每家铺子的主人都说:“这是手绣的。”不论是布袋,钱夹,手提包,千般万样,紫绿青橙,竟看得不当一回事起来。匆匆地走了,连这城,也不当一回事起来。
如今坐在黑夜里想起,何等懊悔当日的轻慢,那些花枝缠绕的布片,和争争作响的银镯子,以及那条浸在细雨里湿搭搭的狭仄小街,够我作多年的谈资。
如同那个一样叫着凤凰的女子,我谈起她时,总是两眼发亮,三成艳羡七成嫉妒地一口咬定:造物如此眷顾此人,世间形容一个女子的好名词,她不是占尽十成,也占定九成了。
这个女子,亦是向来颇有声名。自然,她不是楼兰美女,没有凤凰城三千年这样久的历史。然而网络一年抵得十年,三四十年下来,以她的才情,名声不盛都不行。她由古诗词起笔,散文,小说,一路写下来,到末了,竟是沉寂得无一字一句了。可惜那些美好的字句她竟不再组织,我问她:在做些什么,又何以不再写,答曰:网上搜寻了所有黄碧的书,镇日便沉浸其中,不亦乐乎……看到何时方了?不知。不写什么,这样不也很好么。
起初,是豆家姐妹一篇篇找来——亏得她们云游四海,不似我这般枯坐井底,不然我终身都只认那只井口是天了——有《销魂误》《唤真记》《魂离》……豆子且端庄地在标题前注上:菊斋女史清玩。我打开看了,象初识福时那样茫然地问:这个,竟也出自不见经传的笔底?
如何不是!可惜此时,她已是转身背对韶华的身影。
遇见她的机会少之又少,要辗转打听才从混无际涯的网络中捞出这个人来。此后,这个淡薄的影子方渐渐清晰,终于竟清晰到了——可以看到她由屏那方打一行字出来,带一个“微微一笑”的表情,问我:菊斋是你做的么?
去秋九月,她来时海水已渐渐凉了,我们站在华联的门里门外互相问对方到了没有。然后看到她,修长的黑裙,头发在脑后随便扎住,但即使是那样素仍然教我吃了一惊:文章已是这样好,人怎么可以还这样漂亮?
很久以后她问我:你怎么能这样镇静,我惶恐得差点绊自己一跤。我大笑,素昧平生,突然要打照面,我这个木讷的人,简直不会走路,不会说话。如果她说的是真的,那么那晚我们一定是相互搀扶着仓皇离开了华联门口。
多久以后有人问起,我都会记得鹭江的露天茶座上,衬着楼顶平台的万丈灯火,她侧对我坐着,所谓温柔,所谓风情,所谓优雅拂人,那时都一一有了解释。
多久以后有许多人在黑夜里问我:凤凰美么?肯定地答他:非常美。
对方不置信地再问:怎么个美?
“下颌很尖,眼色很艳,……”这是别人曾经的形容。
于我,我想了又想,翻来覆去只是一句话:一只锦绣凤凰。听的人总是茫然。
到处搜了她的旧作来看。如何穿了吊带裙去打猎,如何剪了流苏作披肩,如何一段一段地捉摸《情史》里别人的故事。都是些细碎的女儿私语。然而,还有着“凰也生平狂逸惯,素服难入时人眼”的清狂。
她喜说:做人须得七分便止。然而过一些时,她又换了“灼灼”这般艳到十分的名字。
再过一些时见她时,哑然失笑了:仍然换了旧名,做了凤凰儿。
作者:任淡如
本文原创首发。欢迎个人扩散、转发,公号转载请联系开白授权。
▼
深浅之间有淡庐
隐居于文字之间
- 0000
- 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