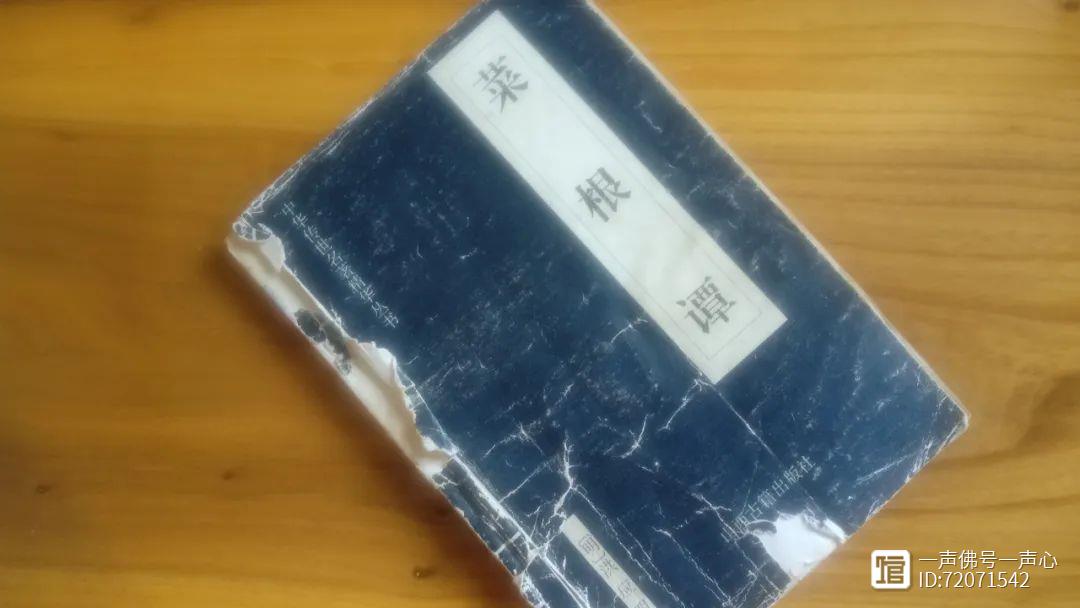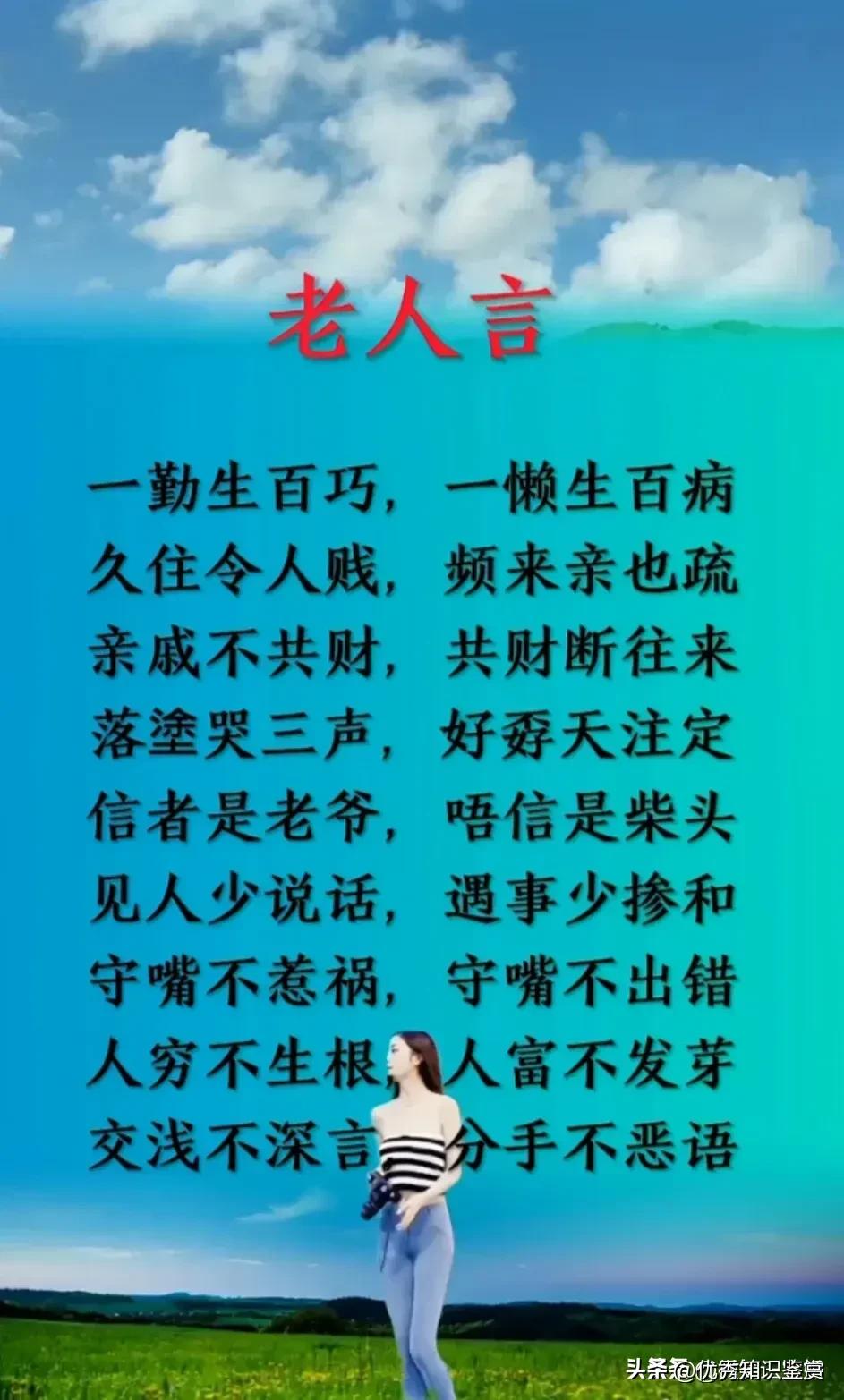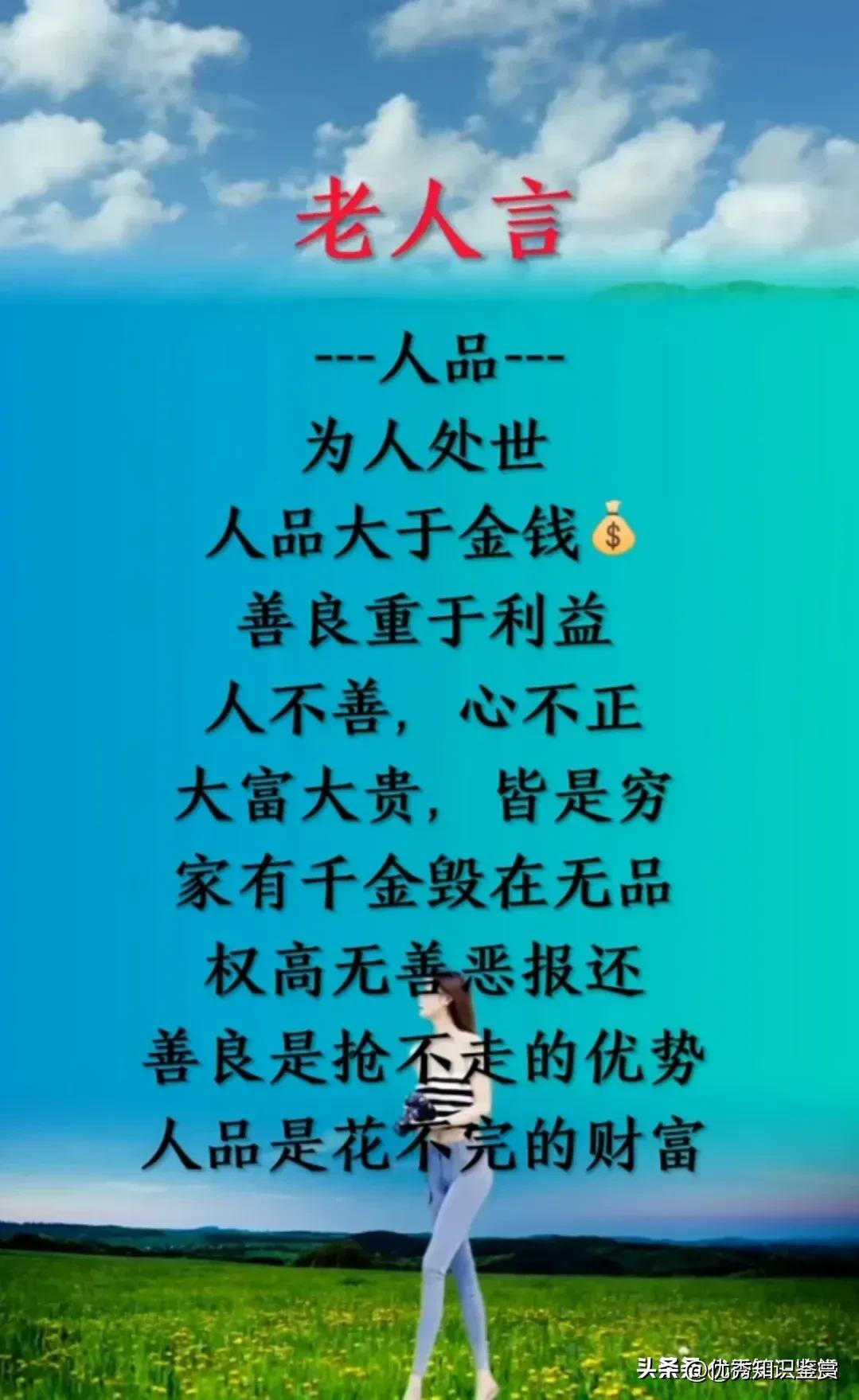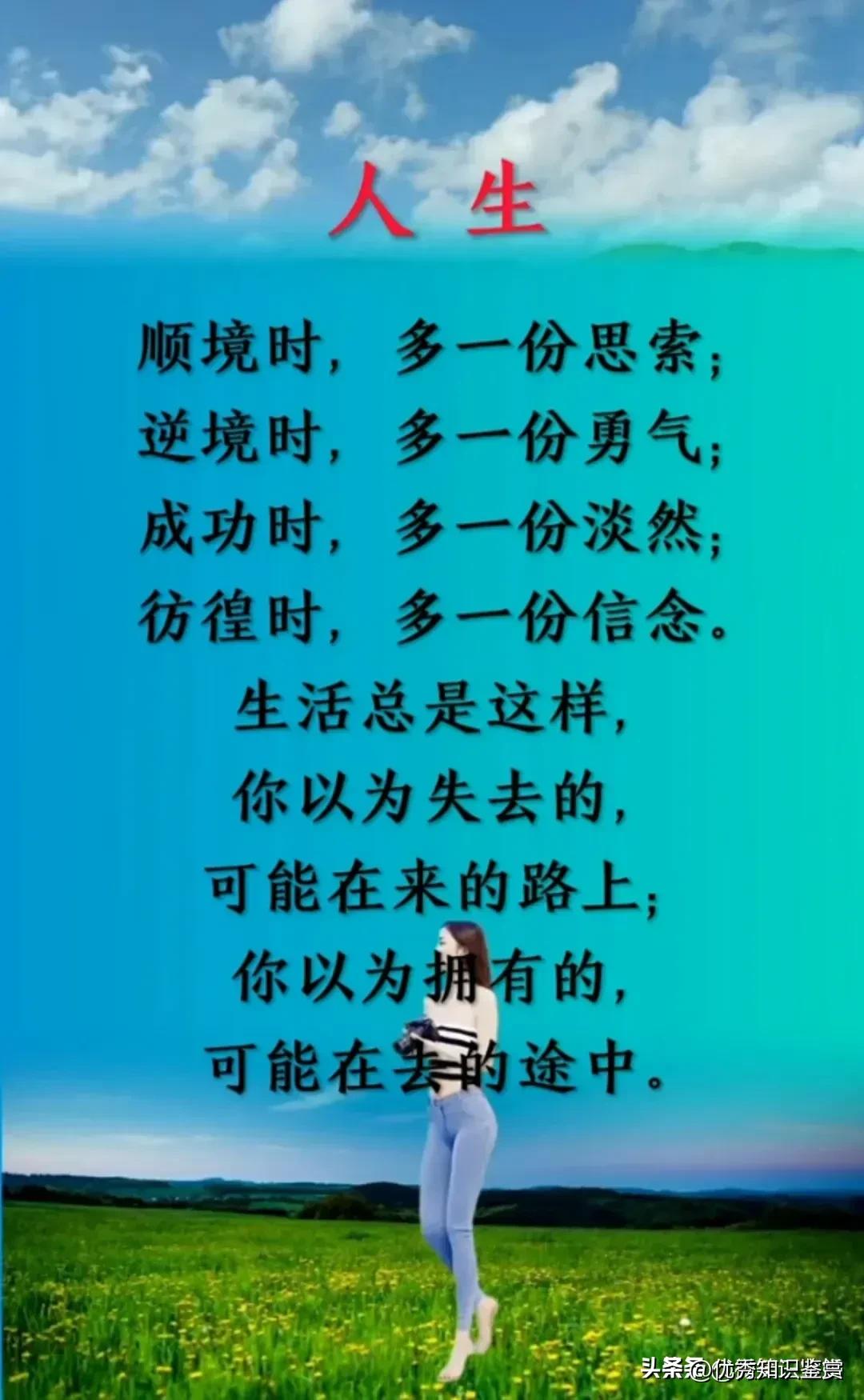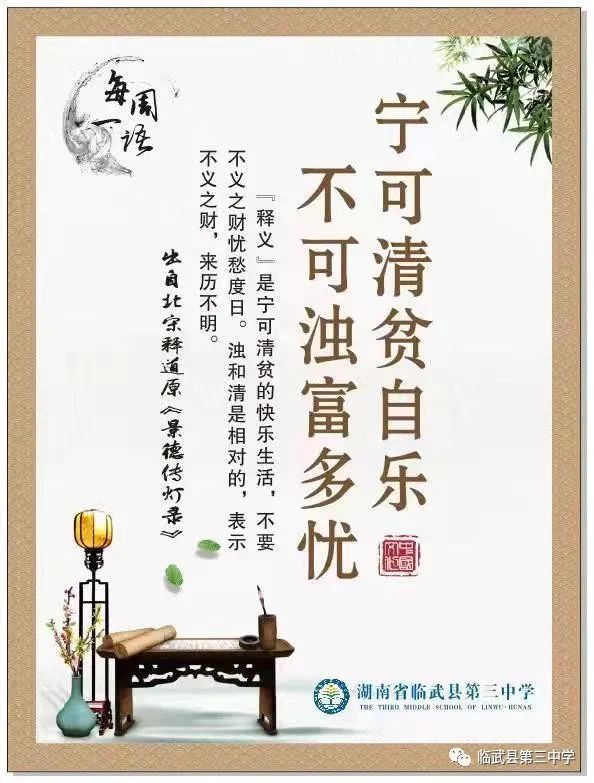牟昆昊丨21世纪20年代水族古籍整理与研究情况简述
注:本文节选自《中国民族古籍70年》(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23年)第六章,此为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该书为准。感谢牟昆昊先生授权发布!21世纪20年代水族古籍整理与研究情况简述
牟昆昊水族自称“睢”,他称“水家”、“水家苗”等。1956年12月21日,国务院“同意将水家族更名为水族”,至此确定了“水族”这一固定称谓。水族主要分布在黔南桂北比邻的龙江、都柳江上游地带,相对应的行政区划是贵州省的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以及广西壮族自治区北部的河池地区。水族居住相对集中,三都水族自治县是全国唯一的水族自治县。据2010 年人口普查,全国水族人口有411847 人,贵州境内水族人口348746 人,占全国水族总人口数的84.68%。水族有古老的文字,水族称其为“泐虽”,他人称其为“水文”、“水字”、“反书”等等。水族文字是一种借鉴汉字构形的方块字兼图画文字,以表意为主。它与汉字有密切联系,同时又有自己独到的特点。历史上的水族先民使用水书文字写下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其内容涉及宗教、哲学、历史、伦理、天文地理、医药卫生、文字艺术等诸多方面。水书文献多由水书先生使用和保存,民间并不普及。由于缺少广泛的社会基础,水族文献长期以来面临着濒危与失传的危险。水族古籍的系统专业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90年代,之后进入到研究的蓬勃发展阶段。进入到21世纪第10个年头之后,水族古籍的整理与研究承续之前的发展态势,又有了诸多新特点。作为贵州省的少数民族文化名片,水族古籍的关注程度一直保持高涨,学术会议召开不断,论文著作层出不穷。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中央民族大学古籍所、贵州民族大学水书文化研究院、黔南师范学院、三都县档案局、荔波县档案局等单位或机构,水族古籍研究人员最为集中,也是诸多会议、活动、研究作品的主要组织者和生产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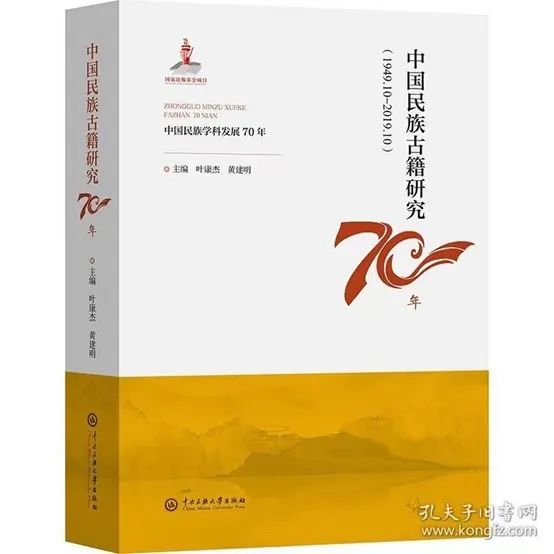
会议方面,从2010年至2019年,除了对水书古籍的翻译、整理、研究外,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荔波县等地,由政府出面持续组织了水书文献搜集、整理和保护工作,制定了一系列相关法律法规,召开了多次水书古籍学术研讨会。其中,每年的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年会,是水族古籍研究学者与全国民族古籍工作者交流学术的重要平台。而贵州水家学会年会,则是省级水族古籍研究的重要交流平台。除此之外,各种地方性会议、政府组织会议也促进了这一阶段水族古籍研究的进程与规范。比如2016年10月18日——21日在贵州三都召开的“水书习俗与殷商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由贵州省民族宗教事务局、贵州民族大学主办,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人民政府、贵州省民族古籍整理办公室、贵州民族研究院、贵州民族大学水书文化研究院承办。该会议积极探讨了水书古籍的来源与发展,有着积极的学术意义;而2017年7月18日在贵州都江镇召开的“水书及水书传承人普查工作推进会”,则可以看作政府鼓励、规范水书古籍研究的典型事例。会议指出,水书作为三都水族自治县独有的少数民族文化,水书申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工作任务艰巨,工作难度大,但要做到不忘初心,继续打好水书这张有利的名片,充分利用县庆的契机,认真做好都江水书普查相关工作,为水书申报打好基础;另外,2019年12月17日在黔南州召开的“水书学术研讨暨申遗工作交流会”,则是为加快推进水书申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工作而进行的努力。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2016年获批的《中国水书国际编码提案》,该提案由潘朝霖、赵丽明、赖静茹等专家学者组成申请团队,2014年在斯里兰卡提交提案,2015年在日本松江会议得到受理,2016年美国圣何塞在修正补充后水族《中国水书国际编码提案》获得通过。水族文献通过国际编码申报,对水族古籍的宣传,文献整理的规范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著作方面,回顾之前研究情况,总结历史研究进程的研究综述类作品开始出现,突出代表就是《中国民族古籍研究60年》(2010年)和《中国少数民族古籍保护与发展报告(1982-2012)》(2013年)。《中国民族古籍研究60年》中的水族部分,将20世纪50年代至21世纪初的水族古籍研究进行了概览式的梳理;《中国少数民族古籍保护与发展报告(1982-2012)》中的《水族古籍保护与发展报告》,从古籍工作的理论与实践、古籍保护、古籍翻译整理与科学研究、学术交流、困难与问题、经验与教训、建议与展望等多个角度进行了回顾与总结。而影印、翻译与整理类研究成果,为水族古籍十年来研究成果最为丰富的部分。主要有:陆春等的“中国水书译注丛书”《婚嫁卷》《麒麟正七卷》《正五卷》《金用卷》《秘籍卷》、《起造卷》等(2010年—2019年),陆春等的《水书·九星卷》(2015年)、《水书·九喷卷》(2016年),潘中西的《水书·六十龙备要(上下)》(2017年)、《水书·吉星卷》(2017年),王传福等“荔波县馆藏精品水书译著丛书”《金银择吉卷》(2017年),赵丽明的《清华大学馆藏十本水书解读:水汉对照》(2018年),韦章炳等的《水书·太平卷》(2019年),陆常谦的《水书·金堂卷》(2019年),梁光华、蒙耀远等的“珍本水书校释丛书”《八宫取用卷译注》(2019年),陆春等的“中国水书”《春寅卷》(2019年)、《降善卷》(2019年)等。除此之外,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与古籍研究所、国家民委少数民族古籍保护与资料信息中心合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字珍稀典籍汇编》(2017年)水族部分也是精彩的水族古籍影印书籍。就水族古籍的影印、整理、翻译而言,近十年有了以下特点:首先,新型拍摄、复刻、影印技术的使用,使水书古籍更加真实地呈现出来,其文献学上的价值不言而喻;其次,翻译整理作品由影印部分、四行译注部分、扩展研究部分的规制被普遍运用,制作精良,整理规范的作品层出不穷;最后,整理翻译的水书古籍选取面不断扩大,出现不少大部头、多册数的水书翻译系列丛书。研究、介绍类著作主要有:贵州省档案馆、贵州省史学会的《揭秘水书:水书先生访谈录》(2010年),陈思的《水书揭秘》(2010年),罗世荣的《水书常用词注解》(2012年),梁光华的《水族水书语音语料库系统研究》(2012年),三都水族自治县的《水书传承人名录》(2012年),韦章炳的《水书文化与中华断代文明——水书历史档案文献探究》(2012年),潘淘洁的《水书绘画书写艺术》(2013年),CCTV《走近科学》栏目的《解密中国:水书之谜》(2014年),唐建荣的《水书:抢救保护与利用研究》(2016年),韦宗林的《水书赋》(2017年),潘一志的《民国荔波县志稿》(2017年),卢延庆的《黔南水书传承研究》(2017年)等。除此之外,有贵州民族大学水书文化研究院组织、潘朝霖主编的《水书文化研究》论文集,一直在约稿、编纂、出版,至今已出版到第八辑,成为水族学者,乃至南方民族古籍学者交流的优秀平台。综上,水族古籍的研究不仅在深度上有进一步的发掘,不少学者还从不同角度扩展着水书的内涵与外沿。最近十年,水族古籍研究相关的论文也层出不穷,当然水平也参差不齐。在我们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搜集到以下篇目的论文:张霁的《谈水书的研究和应用》(2010年),郑高山等的《基于Windows IME水书文字输入法的设计》(2010年),戴建国等的《水书不能普及的多维度分析》(2010年),饶文谊等的《明代水书泐金·纪日卷残卷水字研究》(2010年),廖崇虹的《水书文化开发性保护的产业化发展战略研究》(2010年),农建萍等的《象形文字的活化石——水书》(2010年),罗春寒的《水书传承式微原因探析——以黔东南州丹寨县高寨村为例》(2010年),陈思的《水书文字的兼容性探索》(2010年),欧阳大霖的《水书旅游产品开发的意义》(2010年),陈琳的《水书之仿木刻版本》(2010年),蒙耀远的《水书习俗及其文化内蕴》(2010年),蒙熙儒的《水书日常运用点滴》(2010年),蒙熙林的《水书抢救的政府作为与民间行为紧密结合》(2010年),蒋国生的《“水书”定义之见》(2010年),姚覃军的《水书翻译刍议》(2010年),韦世方的《从水书结构看汉字对水族文字之影响》(2010年),韦章炳的《水书内容的“气”与“坟”》(2010年),潘忠黎的《水书抢救工作扫描》(2010年),梁光华等的《连周共易风情古 水汉同源文化昌——黔南民族师范学院水书文化研究巡礼》(2010年),潘兴文的《无闰水书历法试探》(2010年),韦仕钊的《水书历法对民众生活的影响》(2010年),罗春寒的《水书传承式微原因探析——以黔东南州丹寨县高寨村为例》(2010年),韦宗林的《谈水书的古文字笔画元素》(2010年),潘朝霖的《水书地支多种读音探析》(2010年),牟昆昊的《水书“二十八星宿”声母总结分析》(2010年),白小丽的《水书正七卷纪时地支的文字异读》(2010年),唐建荣等的《水书蕴含的水族哲学思想解读》(2010年),陈思的《水书文字兼容性的探索》(2010年),王炳江等的《水书启蒙拜师仪式调查研究》(2010年),韦荣平的《都匀市水书文化传承调查研究》(2010年),戴建国的《水书与水族社会记忆》(2011年),陈琳的《水书的研究现状及申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述略》(2011年),韦荣平的《水书鬼名文字研究》(2011年),王炳江的《水书启蒙拜师祝词研究——以榕江县水盆村为例》(2011年),李纪英的《公共图书馆保护地方文化遗产的实践与探索——以黔南州图书馆参与水书数据库创建实践活动为例》(2011年),吴苏民的《“水书易”的民族文化遗产价值》(2011年),黄千等的《水书字音编码研究》(2011年),戴丹等的《水书水字可视化输入中的模式匹配》(2011年),蒙耀远的《构建水书学学科的思考》(2011年),吴苏民等的《水书易是贵州最具特色的民族文化遗产》(2011年),蒙耀远的《略论水书中的阴阳五行》(2011年),牟昆昊的《水书“公”、“子”诸字形相关问题的思考》(2012年),王炳江的《水书启蒙拜师祝词押韵特点初探》(2012年),孟师白的《水书、周易、九星的数据对比研究》(2012年),潘朝霖的《水书师认为卵崇拜启示产生太极图》(2012年),蒙耀远的《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水书古籍概述》(2012年),瞿智琳等的《水书传承与发展影响因素的深层思考》(2012年),牟昆昊的《水书天干地支与商周同类字形的比较研究》(2012年),戴建国等的《水书与水族阴阳五行关系分析》(2012年),张振江的《水书脱离迷信凸显民俗》(2012年),潘朝霖的《水书充满阴阳制化的哲学思想》(2012年),文毅等的《解读水书·阴阳五行卷》(2012年),蒙耀远等的《水书与易经的章法结构对比探究》(2012年),蒙耀远的《水书研究的困境与出路》(2012年),荀利波的《基于文献学的古敢水族族源考》(2012年),陈怀义等的《1980—2009年我国水族文献研究的计量分析》(2012年),瞿智琳的《水族水书传承探析》(2012年),吴彩虹等的《谈水书的书法艺术美》(2012年),陈笑蓉等的《水书键盘输入系统研究与实现》(2013年),潘永行的《水书美学价值初探》(2013年),林香等的《水书文本整理问题初探》(2013年),罗俊才等的《水书异体字机器翻译的自动获取方法》(2013年),瞿智琳的《水书档案存续研究》(2013年),林伯珊等的《论中国水族水书文献资源的系统征集》(2013年),龙光鹏的《贵州水族“水书”民俗钱币探秘》(2013年),周崇启的《结构与过程缜密
敬畏和教化并存——试论水族水书教育的内容、形式及其功能》(2013年),蒙耀远的《水族铭刻类古籍搜集整理架构述略》(2013年),尹辉的《活着的甲骨文——水书》(2013年),韦荣宪的《试论水书文化在校园中的保护与传承》(2013年),王海楠的《贵州水书数字化展示系统设计与实现》(2013年),张国锋等的《结合字符特征和FCM的水书文字粗分类》(2013年),王炳真等的《潘光雕:坚持水书传承梦》(2013年),龙平久的《略述水书先生的拜师仪式》(2013年),刘凌的《水书常用字典评述——兼谈民族文字字典理想的编纂模式》(2014年),韦章炳的《浅议贵州水书与中华古文明的亲缘关系》(2014年),麻福昌的《关于水书易文化之记忆与思考》(2014年),潘瑶等的《试论水书文化的传承制度及水书习俗的构建》(2014年),杜昕等的《水书档案文献遗产抢救问题研究》(2014年),刘霖映的《水书连山易是真的连山易:初级论据及前提问题——连山是中华文化史续存的第一部大型古籍》(2014年),陆春的《水书先生口头文化的翻译与价值初探》(2014年),蒙耀远的《水书,水族人的精神高地》(2014年),王炳江的《水书启蒙拜师祝词的传承保护思考》(2015年),华林等的《贵州黔南州国家综合档案馆水书档案文献遗产集中保护案例研究》(2015年),秦珊珊的《水书的视觉文化研究》(2015年),丁时光等的《神秘水书》(2015年),樊敏的《抢救“水书”古籍
促进民族文化多元发展》(2015年),牟昆昊等的《80年代以来水族古籍保护情况概述》(2015年),李黎等的《浅析贵州“水书”文字的形意美》(2015年),崔朝辅的《论水书·丧葬卷中的传统“孝”文化因子》(2015年),瞿智琳的《水书档案编纂现状探析》(2016年),吴凌峰的《荔波县水书抢救保护研究》(2016年),蒙耀远的《水族水书抢救保护十年工作回顾与思考》(2016年),张国锋的《水书古籍的字切分方法》(2016年),陈金燕的《水书传承与发展影响因素的深层探索》(2016年),汪国胜等的《贵州“水书”文献》(2016年),张星的《水书医学文字的造字法分析》(2016年),潘进头的《水书古籍文献中的语言资源及利用研究》(2016年),武志军等的《贵州水书》(2016年),蒙耀远的《水书与水族民间口头文学关系》(2017年),欧蓬迎的《基于传播仪式观的“水书文化”传播研究》(2017年),刘凌等的《民族古文献语料库建设与应用——以水族水书文献为例》(2017年),张欢的《水族碑刻文献的研究现状、价值及保护对策》(2017年),俞俊峰等的《贵州省大数据发展应用促进条例推进三都水书保护与利用的路径研究》(2018年),郑紫阳等的《贵州水书文字在视觉传达设计中的应用基础》(2018年),郑紫阳等的《水书文字审美价值初探》(2018年),张潆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新媒体传播策略研究——以三都水族自治县水书习俗为例》(2018年),梁光华等的《论水书假借水字》(2018年),瞿智琳的《水书档案开发利用研究》(2019年),郑紫阳的《贵州水书文字在视觉设计中的应用研究》(2019年),朱村辉的《水书构型在建筑空间形态设计中的应用研究》(2019年),王琴的《关于水书师传承现状的调查》(2019年),夏春磊的《基于深度学习的水书图像识别算法研究与应用》(2019年),杨秀璋的《基于水族文献的计量分析与知识图谱研究》(2019年),杨秀璋的《基于LDA模型和文本聚类的水族文献主题挖掘研究》(2019年),潘进头的《从水书探寻水族酿酒文化源流》(2019年),杨秀璋等的《基于综合指数和知识图谱的水族文献核心作者群分析研究》(2019年),方琳的《云南水族研究文献的分析和评价》(2019年),陆春的《浅谈水族水书文化的抢救与翻译》(2019年)等。这些论文既有发表在核心期刊的作品,又有刊登在一般刊物、报纸等出版物上的文章,也有硕士论文、参会论文,内容涉及文献学、语言学、文字学、文学、计算机、档案管理、民族学、美术书法等多个角度,一定程度拓展了水族古籍研究和应用的范围。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立项方面,水书古籍相关研究在十年内也多有斩获。具体有:吴贵飚主持的《水族水书传承文化研究》(2010年),王炳江主持的《水书正七卷各抄本的整理和比较研究》(2016年),张振江主持的《水族墓葬碑刻的搜集、整理与研究》(2019年),牟昆昊主持的《水族古籍的整理与文献学研究》(2019年)等。综上所述,水族古籍研究在这十年里有着以下特点:首先,上一时期制定的政策制度、设立的机构、培养的人才,在这个十年里初显成效,水族古籍的保护力度不断加强,水族古籍的价值认识深入人心,水族古籍的新生力量不断涌现;其次,水族古籍的研究已由政府主导和学者自主研究并立的局面,开始偏向学者自主研究,其研究成果更加带有自由度,出现了诸多新的研究思路和研究角度,这表明在水族古籍逐渐脱离濒危情况之后,学者的研究视角已从抢救保护转移到了研究利用;再次,水族古籍研究在高校、科研院所等机构的培育下,出现了一批年轻力量,这些新鲜血液利用专业知识,在文字学、计算机录入编程、档案学角度对水族古籍进行研究,发表了不少论文,出版了不少著作,研究项目也得到诸多立项;最后,水族古籍的研究,目前仍处于翻译整理、扩展运用的阶段,翻译注释的水族古籍很多,但是关涉水书古籍核心的、基础的文献学研究还十分稀少,从目录、版本角度对水族古籍进行梳理和分析,并总结规律的研究成果目前仍然较为空缺。针对水族古籍研究的这一情况,较为妥帖的办法是研究人员将研究中心偏移到文献学角度,在系统学习汉文献学专业知识和方法的基础上,运用于水族古籍研究,会在版本鉴定、流传特点、抄本字体等水族古籍研究上带来系统且更为科学的认识。时光荏苒,岁月穿梭,相信水族古籍研究在之后会更加繁荣发展,进入成熟结果的阶段。
- 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