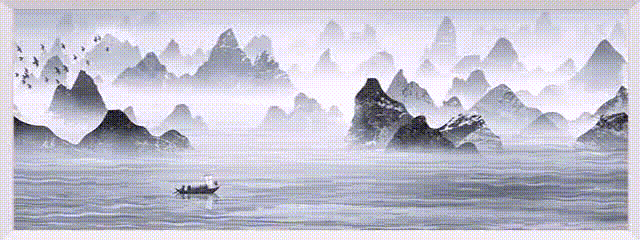薛宝钗真的不喜欢花儿粉儿吗?当然不是,原因令人难以置信
红楼梦的第8回曾经借薛姨妈之口提到宝钗的“古怪”之处,原文说:“(见薛姨妈要给姑娘们宫花,)王夫人道:'留着给宝丫头戴罢,又想着他们作什么。’薛姨妈道:'姨娘不知道,宝丫头古怪着呢,她从来不爱这些花儿粉儿的。’”通部红楼梦,我们的确能看到,宝钗对于“花儿粉儿”这些装饰物,的确并不感冒。书中有限的几次描述宝钗的穿着当中,她都喜欢穿颜色很浅,也不太显眼的衣服。在芦雪庵联诗一回,大观园的姐妹都是“一色大红猩猩毡与羽毛缎斗篷”,余下的姐妹除了身为寡妇必须穿冷色调衣服的李纨之外,只有宝钗穿的是一件“莲青斗纹锦上添花洋线番羓丝的鹤氅”。此外,宝钗的房间也是极为简陋的,原文是“及进了房屋,雪洞一般,一色玩器全无,案上只一个土定瓶中供着数枝菊花,并两部书、茶奁茶杯而已。床上只吊着青纱帐幔,衾褥也十分朴素”。除了这两处作者通过与其他人对比,单独强调宝钗的穿着和房屋装饰以外,一些私下的场合,宝钗的穿着也比较朴素,例如刚刚提到的周瑞家的送宫花一节,此处宝钗的穿着是“家常衣服”;后文宝玉探望宝钗时,对她的穿着也有描写,原文对她的衣饰描述是“蜜合色棉袄,玫瑰紫二色金银鼠比肩褂,葱黄绫棉裙,一色半新不旧,看来不觉奢华”。宝钗在书中的色调,一向是朴素而低调的,鲜有亮色。就连宝钗最重要的配饰金锁,也不是挂在显眼之处,而是被她藏在里面的大红袄上,似乎生怕被别人看见了一样。因此,大家普遍能够得出结论,宝钗确实是不喜欢繁复的装饰和浓艳的颜色。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

小说的第36回,宝钗中午来到怡红院,看到袭人正给宝玉绣肚兜。这是一个“白绫红里的肚兜,上面扎着鸳鸯戏莲的花样,红莲绿叶,五色鸳鸯。”看到这个肚兜,宝钗的第一反应是:“嗳哟,好鲜亮活计!”这可不是宝钗言不由衷的话,而是发自内心的赞叹。因为随后袭人离开以后,宝钗就因为这个五色鸳鸯戏莲的肚兜,“只顾看着活计,便不留心,刚刚的也坐在袭人方才坐的所在,因又见那活计实在可爱,不由的拿起针来,替他代刺”。未婚女孩坐在表弟床边绣鸳鸯,这基本上是宝钗全书当中最大的失态之一。而这次失态的直接诱因,竟然是一个一般说来极不符合宝钗审美的肚兜。不仅此处,再往前翻,还能看到第27回当中宝钗扑蝶的名场面。文中对蝴蝶的描述是,“一双玉色的蝴蝶,大如团扇,一上一下,迎风翩跹,十分有趣”。对于一支宫花也不肯簪的宝钗来说,这样一双蝴蝶虽然美丽,却不太可能有什么能让她“蹑手蹑脚的,一直跟到池中滴翠亭上,香汗淋漓,娇喘细细”的吸引力。然而实际上,宝钗却就因为这一对美丽的蝴蝶,贡献了她全书当中最有名,也是最可爱的一面。这样的宝钗,会不喜欢花儿粉儿吗?其实,对于这个问题,曹公已经从多个角度给了我们解答。之前的文章当中,我就曾经提到过,薛父还在世的时候,宝钗的性格其实和我们看见的样子非常不同。那个时候的她,是个“淘气的”,喜欢看牡丹西厢这样的言情小说,喜欢研究绘画,对绘画的颜料、墨纸等器具如数家珍,一身都是“富贵闲妆”,家里有一箱子“这些没用的东西”。薛父的离世,使宝钗转变了性情,她从此摒弃了这些“花儿粉儿”,成为了一个彻底的极简主义者。然而,家庭的变故不太可能直接影响她的喜好,所以,宝钗并不是不喜欢这些东西,而是责任的压制和规训使得她主动放弃了这些肉体的享受。

然而,再往深细想就能发现,即便叠加上薛父离世和家族责任这些原因,宝钗的行为仍然有逻辑断层。因为就算父亲离世,宝钗要扛起家族的重担,那也和她的喜好和装修风格没什么矛盾之处。她完全可以一边扛住家族的重担,一边继续喜欢那些花儿粉儿,喜欢富丽闲妆和美丽又无用的装饰,她完全可以一边在贾府里笼络人心,一边把屋子装修得和宝玉的“绣房”一样华丽呀?实际上,没准这样装饰自身和房间,还更能博得贾母等长辈的喜欢呢?对于这件事,宝钗自己的解释是“如今一时比不得一时了,所以我自己该省的就都省了。……咱们如今比不得他们了,总要一色从实守分为主,不比他们才是。”听上去似乎,宝钗的极简主义是因为经济条件每况愈下?然而再综合其他的文本考虑,却又并不是这回事。薛家是商人出身,缺什么都不太可能先缺钱(当然,后文薛家进一步败落时又是另一番光景了)。事实也是,宝钗尽管不再戴那些“花儿粉儿”,也不再钻研绘画和学问,但这些东西她并没有折变,而只是放在家里。蘅芜苑的装修风格这件事上,也是凤姐把贾家的装饰品先送了来,并不花薛家的钱,宝钗却仍然没有接受。连大观园中的花柳,宝钗本是住在大观园中的小姐,每日都有分例,她却告诉管花柳的婆子说一概不必送。那么,是什么原因,让宝钗宁愿将这些富丽闲妆搁在箱子里吃灰,也不再佩戴和穿着它们呢?又是什么原因,让她放弃免费的装饰品和免费的鲜花,宁愿住雪洞一般的屋子呢?要想弄明白这件事,有一个看似不相关的细节可以参考。

原文的第45回曾写到宝钗的生活状态:“宝钗因见天气凉爽,夜复渐长,遂至母亲房中商议,打点些针线来。日间至贾母、王夫人处省候二次,不免又承色陪坐,闲话半时,园中姊妹也要度时闲话一回。故日间不大得闲,每夜灯下女工必至三更方寝。”不仅如此,在这段文字中还有一段脂批:“'复’字妙,补出宝钗每年夜场之事,皆《春秋》字法也。”可见,不光作者提到的这次,宝钗每年的秋冬季节都是如此度过。湘云被婶母催逼,做针线活到三更天,她谈及此事的反应是“眼圈都红了”;黛玉则更是,没有人催逼她做针线,她的日常便是“每日家情思睡昏昏”,“今年半年,还没见拿针”。而宝钗的辛苦却是主动为之。不光在长辈处省候、在姐妹处度时闲话这些社交行为是她主动做的,就连这些她半夜做的针线也是她主动从亲妈那里拿来的——用现在的话说,宝钗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卷王”。可是,不断在长辈处和姐妹这里刷好感度尚可理解,但日间不得闲,半夜三更还要做针线活,却不仅损耗精力,而且对薛家的经济效益也是很有限的。既然如此,宝钗为何还要如此自苦?这里的反常的努力,再联想到上文她的穿衣和装饰风格,宝钗的行为处处透着一股苦行僧的味道。明明没有必要,明明自己并不喜欢,却仍然要坚持每天熬夜做针线,住在雪洞一样的屋子里,穿半旧的衣服,全身不着富丽闲妆……面对这些信息,我能联想到的词汇有这么几个:卧薪尝胆、警枕励志、悬梁刺股。这些历史故事当中,主人公都是为了让自己时时警醒,时时努力,专门给自己制造了许多的苦难。不论是警枕还是悬梁,从现实意义上讲都是必要性不大的,但却通常有很重的象征意义。这些为了远大抱负而“自苦”的行为,与宝钗的反常行为异曲同工。

可以想见,当宝钗主动拒绝那堆纱精巧的时新宫花,主动送还凤姐送的屋内装饰,主动放弃华丽的衾褥,主动放弃充足的睡眠时,她的这些肉体的束缚和痛苦,也和司马光、越王勾践等人所经历的一样,会时刻提醒她,不能沉溺于那个温柔富贵乡,不能贪图自身的喜乐,因为她的人生,还有更重要的事需要去完成,还有更大的责任需要去担负。然而宝钗的自苦,与司马光等人的自苦,还有本质上的区别。其一,司马光之类的男人,都是为了自己的野心和抱负才悬梁刺股地努力,而宝钗作为一个闺中女子,只能为了家族中他人的幸福和处境而努力,而且即使要努力,也只能是借他人之力来成就自己,也就是“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其二,这些古代励志故事的结局大都光明美好,司马光成了一代史学家,勾践也成功灭了吴国,为自己十年卧薪尝胆画上了美好的句号,而宝钗的努力,却像是西西弗斯推动大石一样,虽然尽了全力,结局却依然潦倒。这样看来,宝钗的苦行,充满了一种与她十几岁的年纪并不相符的悲剧色彩。也许也是因此,宝钗所用的冷香丸也充溢着这样的象征意义,她的体内那些真性情的“热毒”,需要时时用冷香丸的理智来压制。这个过程辛苦非常,她每每服用冷香丸之时,都要用极苦的黄柏煎汤送服。《红楼梦》的核心要义是社会与封建礼教对人性的异化和压制。宝黛悲剧和贾府败落固然是固化的礼教和倾轧的政治之后的结果,但宝钗前期的“不爱花儿粉儿”和后期的“恩爱夫妻不到冬”岂不也是家族利益和礼教压抑的牺牲品?这个牺牲品过于自觉,过于冷静,使得人们往往忘记了——连她自己也未必记得——她的内心也会痛苦,也会流泪。作者:泥娃娃,本文为少读红楼原创作品。
- 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