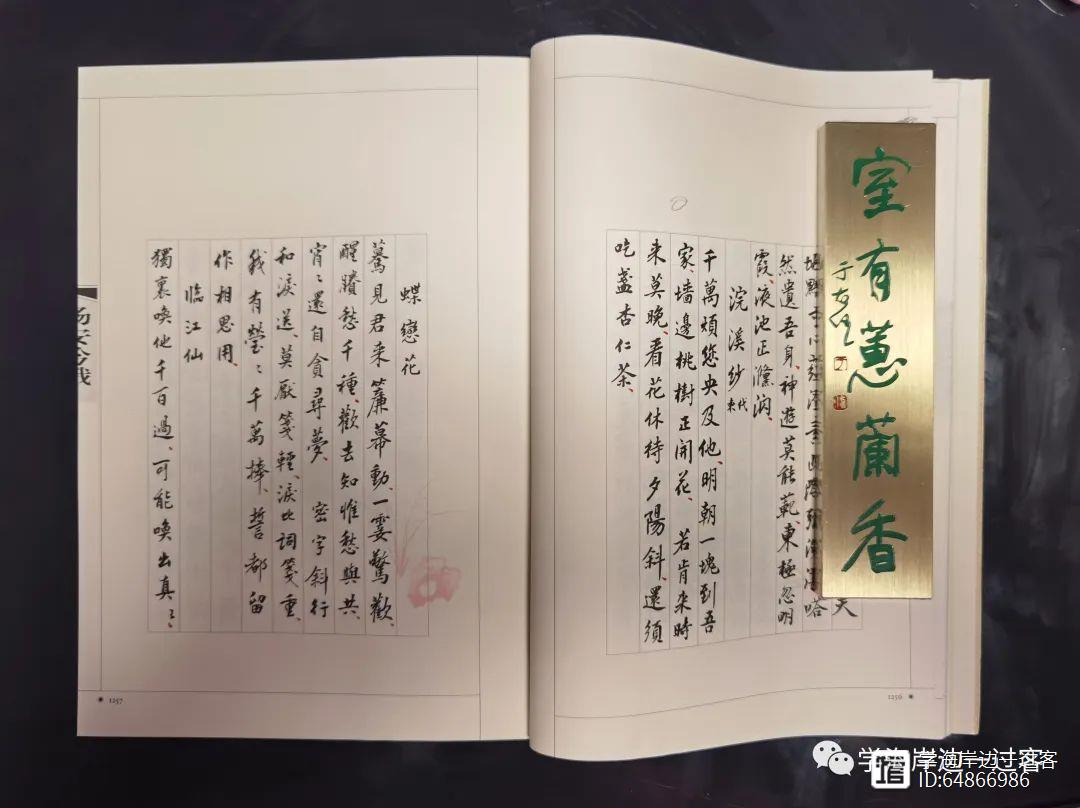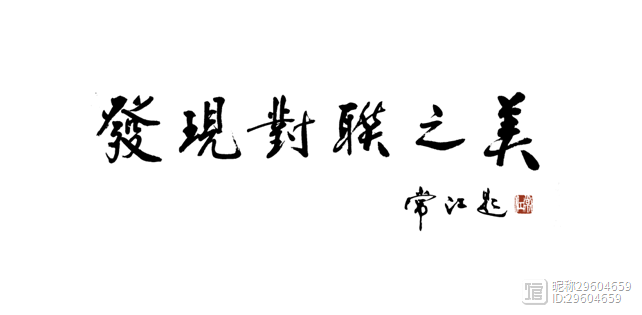古联雅赏(谢青堂)(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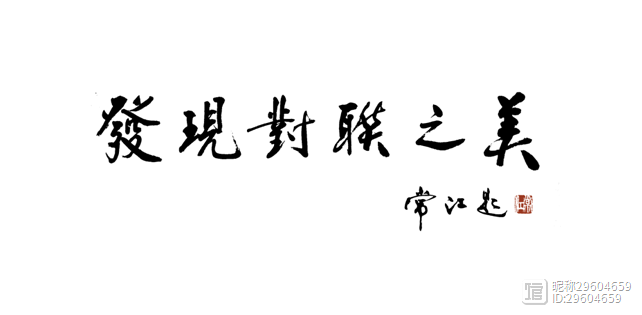


17.
陈逢元一联
仰惊六宇宽,变成几多雨,几多露,几多雪,几多风和雷,时出时入,时往时来,多少神奇谁镇住;
俯视众山小,看破一个嵩,一个衡,一个恒,一个泰与华,自西自东,自南自北,个中底蕴此平分。
此联是题天门山的。吴恭亨评为石破天惊,李青莲见之,当为搁笔。即便我一向认为吴氏评联多有夸张之处,也不得不承认此联用笔汪洋恣肆,不可方物。上联还是人间的眼光,下联则恍如天外飞仙,睥睨万物,有此一烘托,全联立时拔高。五岳见之,渺乎小矣。
18.
吴恭亨贺朱莲溪文燊夫妇五十生日联云:
偕老恰三万六千日;
知非及两四十九年。
这联很有意思。首先,贺人生日联多为单独贺一人,贺双人较罕见,此联无注解,不知朱氏夫妇是否为同一天生日,但很明显吴恭亨在联中是双贺的。另外一个有意思的地方在于,联语极切,切得象作算术题那么的精准。夫妇双双五十岁,那就是一百年,上联即所谓百年三万六千日也,或许我们还可以从读者的角度延伸理解,作者未尝没有祝朱氏夫妇偕老百年之意,如此上联则有双关之妙。
下联同样切双五十。孔子的老朋友蘧伯玉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善于反省,德行懋盛。故后人又将五十岁称为知非之年。此处下联云“两四十九年”是应夫妇同五十岁,兼且含蓄夸夫妇懋德。而这个“两四十九”跟上联的“三万六千”,数字之对巧妙无伦。为之击掌!
19.
谭嗣同一联
云声雁天夕;
雨梦蚁堂秋。
注:《对联话》中附有一段话:沈晓沂绝爱之,以为晶莹凄恻,骨重神寒,但当翦取半江水醮笔书之耳。
晶莹凄恻,骨重神寒,这是古人的说法,我们知道我们的老祖宗们喜欢以感性语言去赏析佳作,往往喜欢将喜好夸大,比如吴恭亨就很喜欢用倚天拔地四字去形容某人联语。这联虽然不是倚天拔地,但是“吐属”名贵是跑不了的了。
这联初看我也无啥感觉,越看就越爱了。也怪,先说联语组句就不一般,云声,云有声吗?雨梦?雨会有梦吗?难道是作者故弄玄虚?非也,云声雁天夕,云声其实是雁声,因为雁在云端,所以作者用了个乾坤大挪移法,把雁之声音套给云了。如果只是言雁声云天夕,合情合理是没错了,但是那种奇警的感觉也就消失了,先言云,后言雁,从看得见的云,听得见的声联想到云端的雁,雁背上的那方天空夕阳,一种从声到景的推进,从细部到阔大的推进。而且雁唳本身有种凄恻的感觉,这种感觉经过天空,夕阳的承载变得更加怆情。可以说完全把景物和作者的情感融合在了一起。
下联同样手法,雨梦其实是蚁梦,甚或是“我”之梦,南柯一梦的典故相信大家都熟悉,淳于棼一梦醒来,发现他梦中赖以建功立业,寻欢得乐的沧海桑田便是堂前一株槐树下的蚂蚁洞而已。而作者在此中加入了“秋”和“雨”的意象,更是透出一种大梦彻悟后的萧萧寒意,落寞无欢。
如此上下联间,空间和时间交集,梦幻与现实对照,神寒毕见。结合当时晚清摇摇欲坠,家国飘摇现状,作者另有深指也未定。骨重或是指此联虽寥寥十字,而内容承载丰富,无一字虚放,字字为骨。晶莹二字评语,是我最同意的。十个字单独分开来平平无奇,但是合一起立刻发生了我们所难以解释的非化学非物理反应,看起来每个字都是实字,但是仔细想去每个字也都是虚字,因为作者的真实意图并不在联语描写的景中,景只是境的门槛,最终是要把你带入他心中的那个意境。这些字仿若吉光片羽,生辉,清鸣。是什么感觉呢,是感觉一串珍珠在碰撞,五颗一起碰撞,十颗一起碰撞,每个清脆的声音最后都融入了一个特定的旋律。沈晓沂说要剪取秋水书之,怕亵渎了如此晶莹联语,也真是知音之语了。
20.
岳麓书院讲堂楹联
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数,陟岳麓峰头,朗月清风,太极悠然可会;
君亲恩何以酬,民物命何以立,圣贤道何以传,登赫曦台上,衡云湘水,斯文定有攸归。
注:此处“太极”非道家太极。而是程朱一脉理学的“理”,他们认为“理”完美无缺,凌驾于社会和人之上,彷如太极。理发而为气,气生万物。这就和太极生阴阳两仪,两仪生三才,三才生万物一样。
虽是书院对联,却包含了做人,读书,处世等诸多道理。前三个排比句肃穆工整,后三句则腾挪高妙。章法上,先凌驾于实境之上,抒发作者对人,对道(这里讲的是儒家之道)的感想,最后又落回实处上,切中所题之处。能命中更能超脱,感觉写征联的同志们可以好好揣摩下。
不过相比起来这联的内容显然是更值得学习的,曾看见一位叫胡遂的教授用“忧乐圆融”来解释这联蕴含的人文境界,写得比我好得多,令我亦有“悠然可会”之感,故不敢私藏,直接摘抄如下:上联写心中的快乐。所谓“学达性天”,就是只要自我内在的心性与外在天地的太极,即内宇宙与外宇宙悠然相契,和融一体,那就无处不可安,无事不可乐。而此乐并非世俗之乐,乃儒释道思想境界中的无烦忧之乐。只要实现了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智者不惑的品格,那么面对是非、毁誉、得失等人生问题就自然能够镇定自若、从容不迫,游刃有余,进入一种“世路如今已惯,此心到处悠然”(张孝祥《西江月·丹阳湖》)“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张孝祥《念奴娇·过洞庭》)的境界。
下联写身上的责任。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西铭》),真正的仁者是有一种人文使命感,一种“己饥己溺”“普度众生”的忧患意识的。因此,登台怀远之时,便难免不产生“念天地之悠悠”的任重道远之想,深感自己责任重大,必须担当起历史人生的使命,方才是自己所学所用的归宿,也就是将有限的个我生命,投入到无限的壮阔事业之中,这种以大我忘小我的境界,同样也是一种对人生是非、毁誉、得失的超越。由此看来,非“内圣”无以“外王”,而“外王”也是一种“内圣”的成就。
- 0000
- 0000
- 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