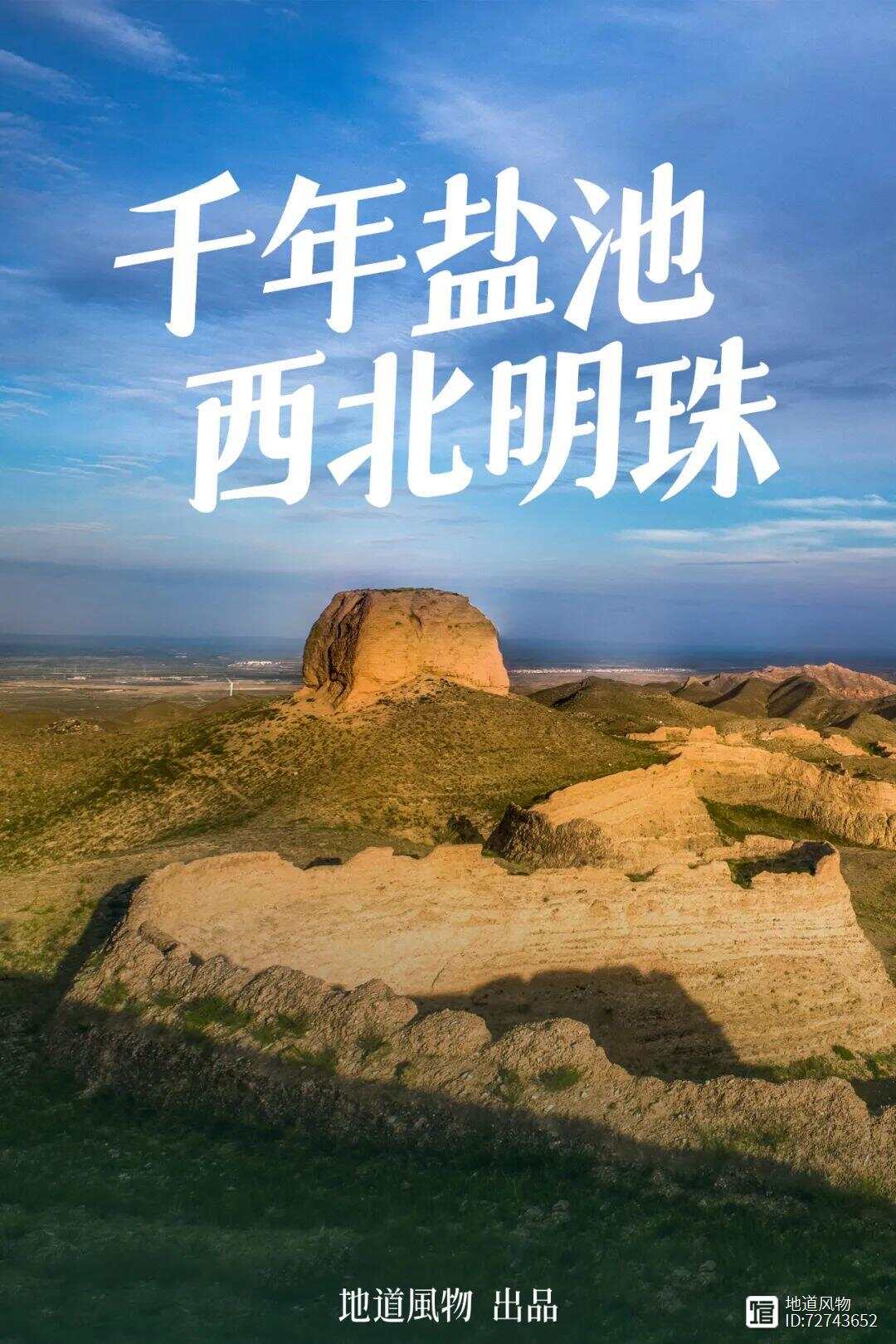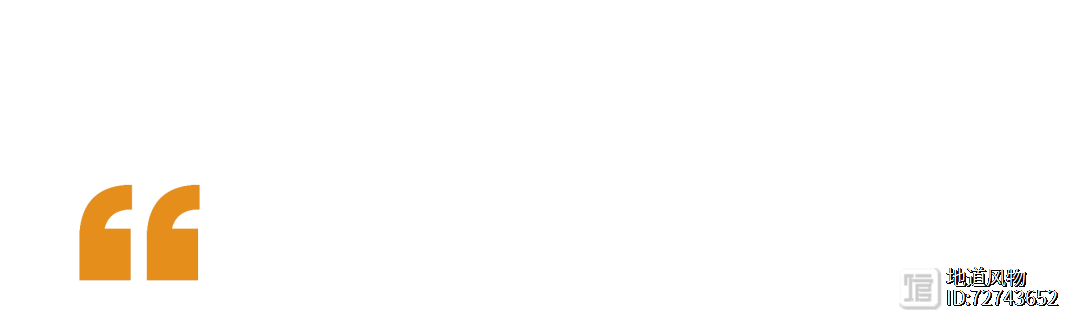【学术观点】公维军 许悦 | “祭必有尸”:殷周“立尸”祭仪探源
摘 要:先秦时期,“祀”(祭祀)与“戎”(军事征伐)是国家治理的两大要务,而祭祀行为又位居其首,初民崇神祀祖以求得庇佑、祯祥的虔诚心理得以彰显。商周时期,盛行以活人代替逝去祖先接受献祭的神圣行为,这便是作为先秦孑遗的“尸祭”现象。殷周初民的“祭必有尸”观念历经“象物”到“象神”的演变,在《肆夏》《仪礼》等典籍中不断活态呈现。随着昭穆制度的确立,“尸必以孙”的尸祭原则被赋予宗法血缘依据。此外,注重模仿与接触的交感巫术思维也一直贯穿在尸祭礼仪中,强化了祖先崇拜的信仰力度。
关键词:象神;尸祭;立尸祭仪;交感巫术
一 殷商时期的“立尸”观(一)从“象物”到“象神”的转变
在前文字时代,初民以图像视觉作为主要认知视觉,其中内蕴的神秘性、直观性、主观性等特点凸显。简言之,初民视野是自然崇拜和万物有灵的“象物”视角,先以自然万物为图像主体,其后才完成从物到人、从人到神的转变。例如,岩画作为前文字时代人类历史的最早形象记录,是初民以象物视角集中勾勒万物的生动体现。在属于中国岩画三大系统之北方系统的内蒙古阴山岩画中出现了日、月、星、云等天体岩画,且带有直观明显的视觉特征:太阳浑圆,中间一点,或四周带有射线;月亮阴柔,呈弯月状;星云连缀,密集小点向四周分散开去。岩画作为朴素视觉表达,所要传达的信息当是“写实”的。再如,北方系统岩画中所绘大量动物近乎都是侧立面像,且常依据刻板视角印象中动物的大小进行放大或缩小式描绘。初民在更接近本原的象征性描绘方式中自觉或不自觉表达出非逻辑的、非概念的象物视角。而眼睛所捕捉到的图像对初民而言十分重要,故一些长期展现出“友好”一面的图像逐渐成为被关注对象,进而被初民虔诚崇拜,甚至成为部落图腾。图腾崇拜作为人类早期普遍存在的初始信仰,也充分体现了初民在认识、改造自然能力低下的情况下,消极转向某一类有益于自身的动植物、无生命体或自然现象,并将其视作血缘亲属以求生存的象物视角。
《左传》所载“夏铸九鼎”传说当为另一生动体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两,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初民将从远方来的各种物象铸于鼎上,一能帮助民众区分神和奸,二能使夏王朝统治者“协于上下,以承天休”。《春秋左传注疏》载:“禹之世,图画山川奇异之物而献之。使九州之牧贡金。象所图物著之于鼎。图鬼神百物之形,使民逆备之。”可见,“象物”“图形”即是模拟物象,所拟之物为“螭魅罔两”。章炳麟《太炎文录·说物》亦载:“诸谲诡异状者通曰物。夏之方有德也,铸鼎象物,物者,罔两螭魅。”鼎上所铸“百物”,是初民基于现世客观表象想象出的超自然存在,或具动物外表,或具某一动物之显著特征。
初民在超自然化动物的同时,又常将其视为异化的祖先,“在人兽同祖的观念之上建构半人半兽的图腾形象,开始重视母祖,但母祖与兽祖是结合的”。在初民意识中,“人”与“兽”虽蒙昧不分,但“人”的主体意识得以彰显。至殷周之时,已出现完全意义上的“象人”具象活动,“人”不仅被独立出来,还被赋予某些职能。《孔子家语·观周》载:“孔子观乎明堂,睹四门墉,有尧舜与桀纣之象,而各有善恶之状,兴废之诫焉。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负斧扆南面以朝诸侯之图焉。”不难看出,孔子观天子宣明政教的明堂时,亲眼看见明君尧舜与暴君桀纣的人物画像,其善恶容貌显而易见。由此观之,尧舜和桀纣的画像被陈设于明堂之内,不仅如孔圣人所言“明镜所以察形,往古者所以知今”,更多当在于以“象”假借其生,拟拖其人,使祭祀有形可依。随着祖先等被祭祀对象的进一步神圣化,初民的祭祀观念开始由“象物”逐渐向“象神”阶段转变,在此时的尸祭现象中表现尤甚。
(二)解“祭”释“尸”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先秦时期,“祀”与“戎”二位一体,是国家治理中最重要的两件大事,而“祀”的地位要先于“戎”,故而祭祀行为在整个国家治理中是不容丝毫置疑的存在。《礼记·祭统》所言“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强调的便是这个道理。在吉、嘉、宾、军、凶五种古礼中,祭祀属于吉礼,位居五经之首。一方面,祭祀范围广泛,“春祭曰祠,夏祭曰礿,秋祭曰尝,冬祭曰蒸。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薶。祭山曰庪县,祭川曰浮沈,祭星曰布,祭风曰磔……绎,又祭也。周曰绎,商曰肜,夏曰复胙。”另一方面,祭祀程序严格,“宫室不设,不可以祭。衣服不修,不可以祭。车马器械不备,不可以祭。有司一人不备其职,不可以祭。”
祭,始见于殷商甲骨文,其古形如只手持肉(

),《说文》注曰:“祭,祭祀也。从示,以手持肉。”晚期甲骨文在下方加“示”(

),意指供奉神主的祭台。《春秋谷梁传·成公十七年》载:“祭者,荐其时也,荐其敬也,荐其美也,非享味也。”“荐”即《说文》所注“荐席”,而荐席即古人用于摆放祭品或跪拜的草席,进而引申为祭奠。以“荐”释祭,可见祭祀的跪拜供奉性质。《春秋谷梁传注疏》载:“无牲而祭曰荐,荐而加牲曰祭。”
祭必用牲,进一步阐明祭用牺牲进行供奉的本质特征。《礼记·祭统》有云:“祭者,所以追养继孝也。”此处的“祭”可理解为通过宰杀牲畜以跪拜的方式敬献于逝去的祖先,进而继尽孝养之道的神圣仪式。周代祭祀以宗庙祭祖为最重,且有“立尸”之惯俗,“自周以前,天地、宗庙、社稷一切祭享,凡皆立尸。”尸,习见于甲骨文和金文,其形似屈膝或侧卧人形(

);于金文中则更像一人垂手扶膝而坐(

)。《仪礼·士虞礼》中郑玄注曰:“尸,主也。”《说文》亦注曰:“祭祀之尸本象神而陈之,而祭者因主之。”因而“尸”特指代替逝去祖先接受献祭的活人。《通典》载:“祭所以有尸者,鬼神无形,因尸以节醉饱,孝子之心也。”用活人代替祖先的行为源于献祭者因鬼神无形而感到心无所托,遂以“有形”替代无形,从而借“尸”尽享佳肴美酒后的满足状以昭示其孝子之心。类似记载又见于《礼记·曾子问》:“祭成丧者必有尸,尸必以孙。孙幼则使人抱之;无孙,则取同姓可也。”尸祭乃孙辈供奉美酒佳肴以飨祖先的祭典仪式,其背后动因可溯及祖先崇拜信仰。
祖先崇拜,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人类信仰文化现象,相信逝去的祖先灵魂仍然可对现世产生影响,是“在鬼魂崇拜的基础上,由生殖崇拜的传宗接代意识,加上图腾崇拜的氏族寻根意识和后起的男性家族观念,而逐渐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其通常意义上指子孙向祖先供奉敬献祭品,以期实现某种愿望或目的。人类学家惯于将祖先崇拜与万物有灵联系起来。英国人类学家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在《原始文化》中指出,灵魂观念是原始崇拜的主要对象,初民认为灵魂可以脱离肉体而存在,且灵魂不死,“神灵被认为影响或控制着物质世界的现象和人的今生和来世的生活,并且认为神灵和人是相通的,人的一举一动都可以引起神灵高兴或不悦”。殷周时期,祭祀之风盛行,然两代祭祖动因与对象又略显不一。殷人祭祖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对灵魂所具神力的敬畏。据殷墟卜辞所载,祭祀对象可分为3类:
甲、天神 上帝;日,东母,西母,云,风,雨,雪乙、地示 社;四方,四戈,四巫;山,川丙、人鬼 先王,先公,先妣,诸子,诸母,旧臣
《礼记·表记》载:“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可见,殷人祭祀“尊鬼”大过于“敬祖”,“人鬼”胜过于“人神”,且祭祀对象有强烈的自然神意味。变幻莫测的自然世界总令殷人恐其源于自我的一举一动,故“努力通过祈祷、献祭等温和谄媚手段以求哄诱安抚顽固暴躁、变幻莫测的神灵”,以期获得神灵的庇佑和赐福。
周代改进了生产方式和工具,生产效率得到有效提升,附加而来的是伴随着生产经验的累积而对自然规律和人本身价值不断进步的认识,祖先崇拜逐渐压倒人鬼、天神崇拜。周人祭祀除希望得到天地之神的庇佑之外,更期望通过祭礼敬孝祖灵以承其福泽。西周尊宗敬祖观念浓厚,尽孝是西周祭祖核心动因,因而周人“把德孝并称,德以对天,孝以对祖”。显然,这与宗法制度联系异常紧密,而宗法伦理的核心就在于堪与“尊天”并列的“法祖”。宗法制下对血缘亲疏的重视使得祖先的地位和神圣性得到加强。
二 、“祭尸”与“尸祭”:从杀人祭礼到活人为“牲”
(一)“祭尸”:早期的“人牲”献祭
周人祭祀重在宗庙之祀,强调“凡皆立尸”。然而,尸祭礼俗起源甚早,《礼记·礼器》有载:“其礼亦然,其道一也。夏立尸而卒祭,殷坐尸,周旅酬六尸。”可见,周人立尸礼俗至少在夏代便已出现,区别在于尸或坐或立。扮演尸的活人在祭祀礼中作为“被祭祀者”,不仅代替祖先接受虔诚献祭,更被赋予禳灾降福的神圣职能。在早期的祭祀活动中,人往往作为献祭者出现,这便是“人牲”。
“人牲”,是祭祀时像牛、羊、豕等牲畜一样将人作为祭品供奉给祖先,区别于“人殉”。殷商时期,先民崇天尚鬼,长期被神权宰制下的鬼神信仰所笼罩,以人献祭较为普遍。殷墟甲骨中出现了大量关于人牲的卜辞,据胡厚宣先生统计,有关于人牲的甲骨卜辞1992条,从迁殷到亡国,如若算上未记录人数的卜辞,至少有14 197人。对此,黄展岳先生指出,盘庚迁殷后,殷人无所不祭,天神、地祇、人鬼(祖先)都是所祀对象。其中,尤以祭祀人鬼最为隆重。殷人不但在埋葬祖先时兼用人殉和人牲,在之后的定期追祭中都会使用人牲。而人牲的来源多是俘虏,尤以西方的羌为主,卜辞中用羌人数高达7 426人,占据人牲总数的一半还多。殷商时期,国力强盛,商王武丁常以武力四处征伐,蛮夷之族相继被降伏。一如《商颂·殷武》所载:“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日商是常。”这一时期,奴隶制也达到了顶峰,统治阶级或贵族就是奴隶主,来自西方游牧民族的羌俘在压制下成为其奴隶来源,但如何处理大量羌奴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正如宗教史学家米尔恰·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的弟子、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布鲁斯·林肯(Bruce Lincoln)在《死亡、战争与献祭》中指出的那样:“在一个劳动力不甚紧缺的经济体制里,罪犯和战俘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难题:或者将他们释放(以后又会形成威胁),或者看守他们(这样不得不供给他们饭吃)。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大规模的农业社会可以把俘虏贬为奴隶……小规模的农耕者和游牧民就没有这样方便的解决办法了。人祭便提供了摆脱这一困境的办法。”事实上,殷商的农业、纺织业、畜牧业虽都有所发展,与周边国家也多有经济贸易往来,但庞大的帝国最终还是要依赖小规模的农耕者创造、积累价值,然囿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大量奴隶与小规模生产并不适配,奴隶最终沦为人牲。
在无文字的史前大传统时代,祭尸现象甚至可追溯到远古时期产生于原始农业崇拜的野蛮人祭习俗。植物考古新发现表明,早在新石器时期,两河流域的先民已开始耕种某些籽粒可以食用的草本植物,到了新石器高速发展时期,农作物已经成为重要的食物来源。而能孕育食物的土地很快成为先民们崇拜的对象,并伴随有某种残忍的宗教仪式——杀人祭谷。叶舒宪先生对此曾有过详尽阐述,并确认杀人祭谷是所有农业典礼活动的原始本相这一结论的可信性。准此,从史前社会的杀人祭礼,到殷商社会的人牲,再到周代以活人为牺牲的尸祭,无论是祭祀的本质还是动因都存在较大差别,这固然是社会发展的结果,但也要看到其彼此承袭的一面。
(二)《肆夏》典乐中的“尸祭”
《周礼·春官·大司乐》载,“王出入则令奏《王夏》,尸出入则令奏《肆夏》,牲出入则令奏《昭夏》”,而“三夏皆乐章名”。在周代“尸祭”礼俗中,“尸”的出场伴随有典乐《肆夏》。《说文》释“肆”曰“极陈也”。其中,“陈”作陈列,意即陈尸之列;“极”本意指房屋最高处,引申为达到极点,喻指处以极刑。《周礼·秋官·掌戮》载:“凡杀人者,踣诸市,肆之三日。”可见,“肆”可指极刑杀人后而陈尸,且须陈尸三日。《礼记·月令》对此亦有记载:“仲春之月……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毋肆掠,止狱讼。”注曰:“肆谓死刑暴尸也。”正义曰:“肆谓死刑而暴尸者。肆,陈也。谓陈尸而暴之。”由此可见,“肆”之杀意甚浓。
我们还可从“厶”视角对“肆”进行深入认知。汉字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载体之一,自诞生之初,便内蕴着古人的思维方式。同时,汉字之所以能够区别于其他文字,是因为其以表意为直接特征。汉字为适应社会文化发展的需要,历经自甲骨文以来的系列演变,使得字形、字体逐渐稳定化和规范化,字意也发生较大的变化,但其仍旧提供了找寻原初之意的可能——某一组成部分。“肆”,偏旁“镸”,其下部为“厶”。对此,叶舒宪先生已在《“公”概念的祭典起源》相关问题阐析中予以生动诠释。我们或可受其启发,进一步探究“肆”承杀戮之缘由。
“公”作为男性符号,同“雄”共同带有阳性符号“厶”。“厶”本义指阳物或阴囊,《玉篇》训“厶”为“甲”。而作为十干之首,甲也被视为阳性力量根源——太阳神的标志,可见“厶”存至阳一面。又《说文》训“公”为“平分”,故“厶”可解释“公”概念的来源,即将神圣阳物所代表的繁殖生育撒播至国土之中,让民众“平分”并享。在一些原始部落的祭典中,不乏用活人做“人牲”、分尸肉以撒大地的血腥礼俗。可见,“公”以“厶”会意,不仅能够体现“共同分享”背后阳性生殖力崇拜与农业生产的关系,更潜藏着原始祭奠的残酷与血腥。结合“尸祭”最早的源流“人祭”及其与农业生产的关系来看,“公”的血腥杀祭色彩相当浓厚。
此外,专指去除阳物即阉割的汉字“去”,其构成要件同样有“厶”。阉割现象,不仅存在于中国古代社会中,也存在于其他地区的社会发展历史中。叶舒宪先生曾将古代的阉割视作一种文化现象,并指出阉割可以作为降低生育率、控制人口的手段而存在,可以作为满足某些特殊的社会性职业需求之手段而存在。但是,阉割现象呈现出对身体处以极刑的血腥特征。阉割下来的阳具脱离身体,男性身体被“一分为二”,这种生理上的可怕变化极有可能导致被阉割者丧命,也更容易从个体心理和社会文化层面令被阉割者“丧命”,而后者是没有流血的杀戮。
如此看来,在古人的眼中,“厶”在其本义的基础上带有浓厚的献祭杀戮色彩。而“肆”所包含的这一符号,喻指杀人并陈尸而暴也就显得更加合理了。尸祭礼中所奏《肆夏》深蕴着宰杀人牲分尸而祀的血腥恐怖意味。反之,也一定程度上指证周代的“尸祭”现象已成为文明逐渐取代野蛮、程序走向完备缓和的产物。
(三)《仪礼》中的“尸祭”
周代尸祭礼俗在《仪礼》中记载最为详尽,又特别集中在《士虞礼》《特牲馈食礼》《少劳馈食礼》三章。其中,《士虞礼》记载的是葬父母之后,在日中时举行祭祀,以安父母之精气和魂魄的正礼,形式较为简单。《特牲馈食礼》是诸侯在宗庙祭祀祖先的吉礼,《少劳馈食礼》是卿大夫在祖庙祭祀祖先的礼仪。尸在祭礼中均扮演重要角色,围绕他们展开的祭礼程序完备,原则谨严。综合来看,“尸祭”礼仪围绕“尸”的程序可分为准备、开场、高潮、尾声4个部分。下文以《少劳馈食礼》为例进行分析:
1.准备阶段:“筮尸”与“宿戒尸”
需要在祭祀前提前11天进行占卜确定祭日是否吉利,如不吉利则从下一旬以外的日子中进行再占卜,直到确定吉日。之后于祭祀前择一合适人选,邀请并告知其于祭祀当日前来。同时,被选定为做尸之人需“不乐不吊”,这样方可达到“齐者精明之至,然后可以交于神明”(《礼记·祭统》)的目的。完成尸的准备工作,主人家便可着手准备祭祀礼所需物品。
2.开场阶段:“迎尸”与“妥尸”
到了祭祀之日,待祭主一切准备妥当后,就需在宗庙之内等待“尸”的到来。巫祝(即祭主赞词者)出庙门引尸,尸到来之后按照礼俗在宗人的伺候下先洗手,然后经巫祝的引导上堂入室。巫祝和祭主向尸行拜礼,并请其安坐。尸向巫祝和主人答拜还礼之后坐下,祭祀仪式正式开始。
3.高潮阶段:“献尸”与“尸酢”
尸安坐席间,化身为祭主的祖先,正式接受祭祀。祭主向尸献上佳肴美酒。席间,尸先取韭菹在豆与豆之间致祭。待尸接过佐食献上的黍稷和肺祭致祭后,再接过脊肺振祭并吃一口,然后吃三口黍饭,佐食又陆续献上肉、鱼、羊、猪后肢上段等供尸享用,先后共11饭。饭食享用完毕开始酌尸,祭主、主妇和宾客依次上前向尸敬酒,祭主敬酒之后可听取巫祝转达祖先的祝福。至此,祭祀核心目的达到,祭礼准备进入尾声。之后主妇敬酒不听取祝辞,宾客敬酒后,祝出室告诉祭主“礼成”,再上前引路,带尸走出庙门。
4.尾声阶段:“送尸”与“食馂”
供养之礼已成,祭主、巫祝出室,巫祝告祭主礼成,然后巫祝再次走进室内,引尸走出庙门。尸出之后,祭主和巫祝再次返回室内,设对席,行源于早期先民共食制的隆重食馂礼,即分食祭品,共享祖先恩惠。至此,尸祭仪式正式结束。
在这场庄重又神圣的祭祀礼仪中,尸虽然作为祖先的替代者,享受着最高级别的供奉,但不过是“人牲”的替换,从活祭品变成了享用祭品的人,并且被赋予“象神”的力量。不得不说到了周代,尸已经是文明高度发展的产物了。尸祭礼俗彰显着周代人文教化的精神旨归,既合乎昭穆之序,又尽显巫之本计。
三、昭穆与巫术:
殷周“立尸”祭仪的承续
(一)“尸祭”与昭穆之制
尸祭仪式的核心在于借尸扮祖,并借尸获得祖先的祝福和庇佑。因此,于殷周先民而言,不论是出于尊祖心理还是现实需要,尸的选择和确立尤为重要。《礼记·曾子问》载:“祭成丧者必有尸,尸必以孙。孙幼则使人抱之;无孙,则取同姓可也。”《礼记·曲礼上》亦载,“孙可以为王父尸,子不可以为父尸”。可见,尸只能由嫡系或同姓孙辈扮演,即使孙辈很小不能独立完成祭礼,也仍由其他人抱着完成。就“为人子者……祭祀不为尸”而言,郑玄注曰:“以孙与祖昭穆同。”可见,选尸要遵循严格的原则与程序,而以孙替祖的做法与昭穆制度关系匪浅。
关于“昭穆”,《汉书·韦贤传》载:“父为昭,子为穆,孙复为昭,古之正礼也。”《周礼·春官·冢人》载:“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为左右。”郑玄注曰:“先王造茔也,昭居左,穆居右,夹处东西。”《礼记·王制》载:“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大(太)祖之庙而七。诸侯五庙,二昭二穆,与大(太)祖之庙而五。大夫三庙,一昭一穆,与大(太)祖之庙而三。士一庙。”《礼记·祭统》载:“夫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别父子、远近、长幼、亲疏之序而无乱也。是故有事于太庙,则群昭群穆咸在,而不失其伦,此之谓亲疏之杀也。”由此不难得知,昭穆可用于墓葬、宗庙,也可用于祭祀,且对应“尸必以孙”的原则。原因恰恰在于若接受祭祀的祖先由子辈扮演,那么尸将接受父辈的跪拜,父子之序被颠倒为子父,“犯顺”则“不祥”,是绝不被允许出现在吉礼之中的。如此一来,由孙辈扮演祖先接受后代的祭祀,不仅合乎父子之序,还能“明子示父之道”。
而昭穆制度的起源,与氏族间的两合婚制不无关系。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认为:“当氏族观念渐次发展的时候,一面因为男子所生的子女不能留在原有的氏族以内,一面又因为有组织这两类子孙的同等必要,所以氏族将很自然地采用成对的形式。如果有两个氏族同时开始出现,则整个结果便达到了;因为属于一氏族的男子和女子,将与对面一氏族的女子和男子互相婚配;其所生的子女则各随着他们的母亲而分配在两氏族中。”由此观之,受两个氏族间的通婚条件所限,父与子分属两个氏族,只有祖和孙才是同一脉。当过渡到父系氏族社会后,父系血统成为亲属系统的根本,同宗同族、同根同源观念愈甚,正所谓“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左传·僖公十年》)。如此看来,昭穆制度除了用以区分父子氏族之外,更为“尸必以孙”原则的确立提供了宗法血缘上的重要依据。
(二)“尸祭”与巫术思维
在神圣的祭礼空间中,尸的出现一转先前祭祀鬼神听之无声、视之无形的无所依托局面。通过让祖先“再生复活”并与祭祀者一同享用美酒佳肴的方式,使其欣然接受后辈的祭拜,进而让赐福、庇佑行为变得更加真切可感。所以,出现在祭典上的尸往往“服卒者之上服”(《仪礼·士虞礼》),从衣着服饰上模拟祖先。英国人类学家弗雷泽(James George Frazer)在《金枝》中提出了以“相似律”和“接触律”为两大原则的巫术——“顺势巫术”与“交感巫术”。前者通过不局限于有意识的模仿达成目标,后者借助于相互接触的物质实体实现目标,而不论该物体是否为该人身体的一部分。
尸在祭祀中的一个显著职能是“象神”,其在代替祖先的同时,在更大程度上是装扮成祖先——尸穿上祖先的衣服便意味着同祖先大致接近乃至等同,这是顺势巫术相似性原则的体现与运用。同样地,尸在祭祀中的另一重要功能是代替祖先借助巫祝之口,将福祉赐予后代子孙。尸既然能够扮演祖先,那么尸的祝辞便是祖先的祝辞,听之可得祖先福泽,这就显得顺理成章了。
但在现实的实践中,“这两种巫术经常是合在一起进行。或者更准确地说,顺势巫术或模拟巫术可以自己进行下去,而接触巫术,它需要同时运用顺势或模拟原则才能进行”。这明显是对接触巫术思维的运用。尸身着祖先的衣服,即达成了接触巫术的首要基础条件——相互接触。按照接触率原理,事物一旦发生接触,彼此之间就会建立联系,并将一直保留着,即使相互远离,联系也依然存在。所以无论对其中一方做了什么,都会对另一方产生同样的影响。《白虎通》载:“祭所以有尸者何?鬼神听之无声,视之无形,升自阼阶,仰视榱桷,俯视几筵,其器存,其人亡,虚无寂寞,思慕哀伤,无可写泄,故座尸而食之,毁损其馔,欣然若亲之饱,尸醉若神之醉矣。”因而在祭典中,尸会因后辈虔诚的祭祀礼仪以及美酒佳肴的享用而产生愉悦感、满足感,这便可等同于祖先的亲身感受。除此之外,分食尸吃剩下的食物也是使用交感巫术思维获得祖先福泽的方式。祖先因有德而被祭祀,分食祭品就如同分享祖先所降福泽与恩惠。
事实上,巫术及其信仰早自上古时代便已存在,历朝历代的文化、政教等均深受其影响,如商代的巫术以占卜为主,凡事问卜成为惯习,希冀求得祯祥、丰稔、出师有名等吉兆,其政治带有鲜明的“巫政合一”色彩。西周以降,礼乐文化的出现强化了政治与伦理血缘间的关系,巫术被逐渐分离出来。尽管如此,积淀着原始想象和宗教神秘体验的巫术思想却不会凭空消失。无论如何,正如荆云波所言,“立尸祭祀是一种宗教行为,尽管附加在其上的孝道伦理、等级礼教的观念非常明显,但这些掩饰不住它所具有的巫术思维,可以肯定,尸祭当中的巫术因素和手段加强了祖先崇拜的信仰力度。”其言甚确。
四、余论
殷商时期的初民祭祀,既重宗庙之祀,强调“祭必有尸”,毕竟尸是祭仪的关键所在;又重天地百神之祀,诚如《朱子语类》所载:“古人祭祀无不用尸,非惟祭祀家先用尸,祭外神亦用尸。”至周一朝,随着滥觞于殷商时期的左昭右穆宗庙之制逐渐确立,立尸祭祀仪式愈加社会化,进而朝着立尸制度化方向延续。受其影响,周人在祭祀天地、社稷、外神等各式场合都会选择用尸,足见三代之时尸祭礼俗之盛。只是秦汉以降,“祭立尸”这一先秦孑遗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最后竟亡失于中原地区,这其中的原因未来仍然值得进一步探讨。
(本公众号删去文章注释,完整版请查阅原刊)
【引用格式】公维军,许悦.“祭必有尸”:殷周“立尸”祭仪探源[J].百色学院学报,2023,36(02):29-36.
作者简介

公维军,山东临沂人。文学博士,江苏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学人类学。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江苏省“双创博士”(世界名校类)人才项目、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等5项;出版学术著作4部;在《民族艺术》《社会科学》《贵州社会科学》《明清小说研究》《社会科学家》等期刊上发表论文近30篇。成功入选2019年度江苏省“双创人才”引进计划。

许悦,云南曲靖人。江苏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主持江苏省研究生科研与实践计划项目等3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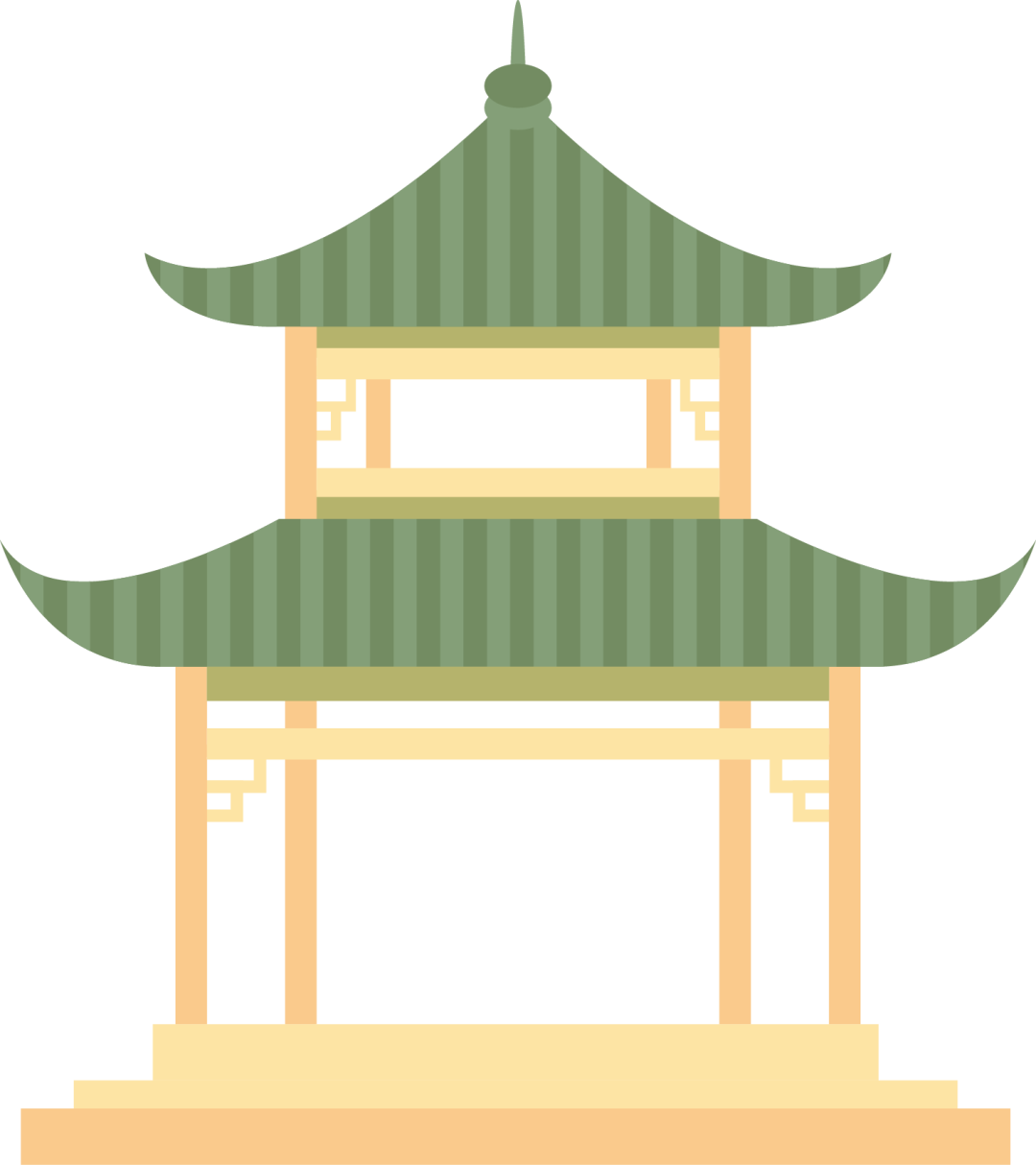
文学人类学
组稿编辑丨黄 玲
审稿编辑丨杨 骊
值班编辑丨翁芝涵
在田野中发现
在书斋中思考
文学人类学研究会主办
欢迎交流:its2011@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