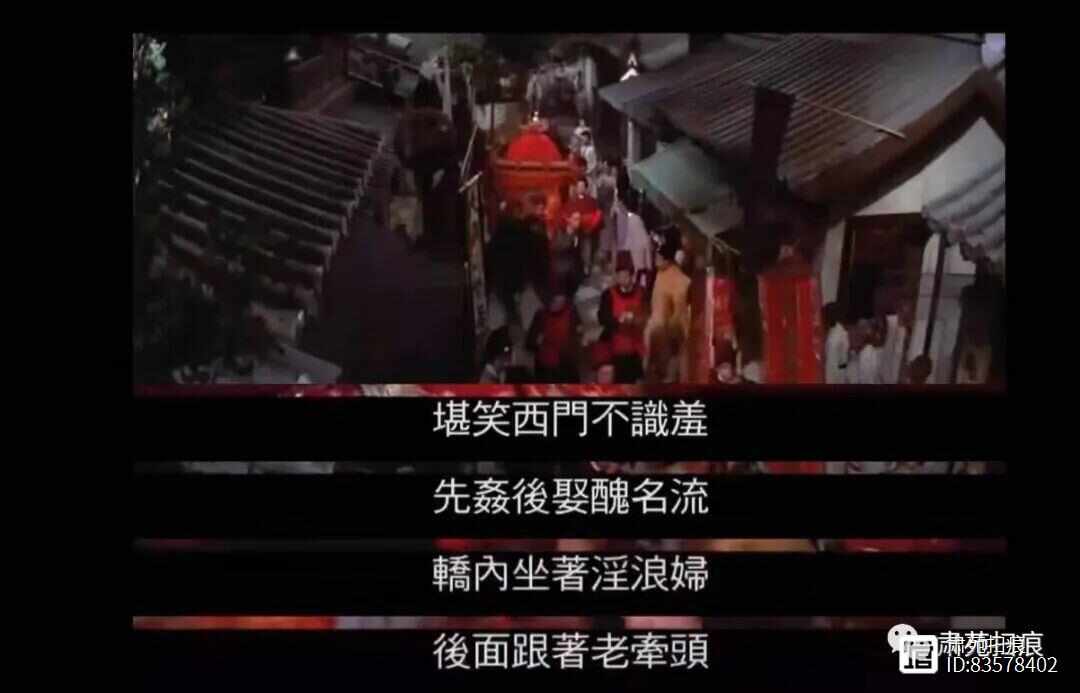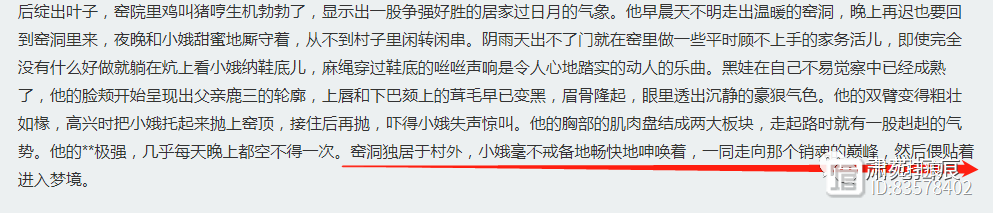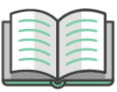弦 声 │从《金瓶梅》到《歧路灯》

《金瓶梅》是我国第一部由文人创作的以家庭生活为题材的世情小说。它给后代的长篇小说创作以巨大的影响。有些承受了它的淫词秽语更走入下流,如《玉娇李》《肉蒲团》等;有些则发扬了它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逐步把我国古代长篇小说的创作推向高峰。
从《醒世姻缘传》《歧路灯》《红楼梦》,我们就可以约略看出这条发展的轨迹来。
对于《红楼梦》所受《金瓶梅》的影响,已有不少专家发表了高论,而对《醒世姻缘传》《歧路灯》所受《金瓶梅》的影响,论者尚不多。
这里仅将《歧路灯》与《金瓶梅》加以粗略的比较,以见二者间的关系。
蒋瑞藻的《小说考证》卷八引一缺名笔记说:“吾乡前辈李绿园先生所《歧路灯》一百二十回,虽纯从《红楼梦》脱胎,然描写人情,千态毕露,亦绝世奇文也。”
这里的记载显然有误,因为曹雪芹开始撰写《红楼梦》要晚于《歧路灯》,李绿园创作《歧路灯》,据栾星先生考证,开笔于乾隆十三年(1748),完成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历时三十年。
实际上李绿园创作《歧路灯》的动因与《金瓶梅》颇有关联。李绿园在《歧路灯・自序》中说:
若夫《金瓶梅》,诲淫之书也。亡友张揖东曰:此不过道其事之所曾经,与其意之所欲试者耳。而三家村冬烘学究,动曰此左国史迁之文也。
余谓不通左史,何能读此;既通左史,何必读此?老子云:童子无知而朘举。此不过驱幼学于夭礼,而速之以蒿里歌耳。
小说第九十回“程嵩淑观书申正论”ー节,作者又借书中人物之口重述了这种看法。
因此李绿园就要反其道而行之,“藉科诨排场间,写出忠孝节烈,而善者自卓千古,丑者难保一身,使人之为轩然笑,为潸然泪,即樵夫牧子厨妇爨婢,皆感动于不容己。……因仿此意为撰《歧路灯》一册,田父所乐观,闺阁所愿闻(《自序》)。
李绿园多次以激烈的贬斥态度在《歧路灯》中提到《金瓶梅》,从而给我们提供了许多这部书在清代社会上的流布及影响的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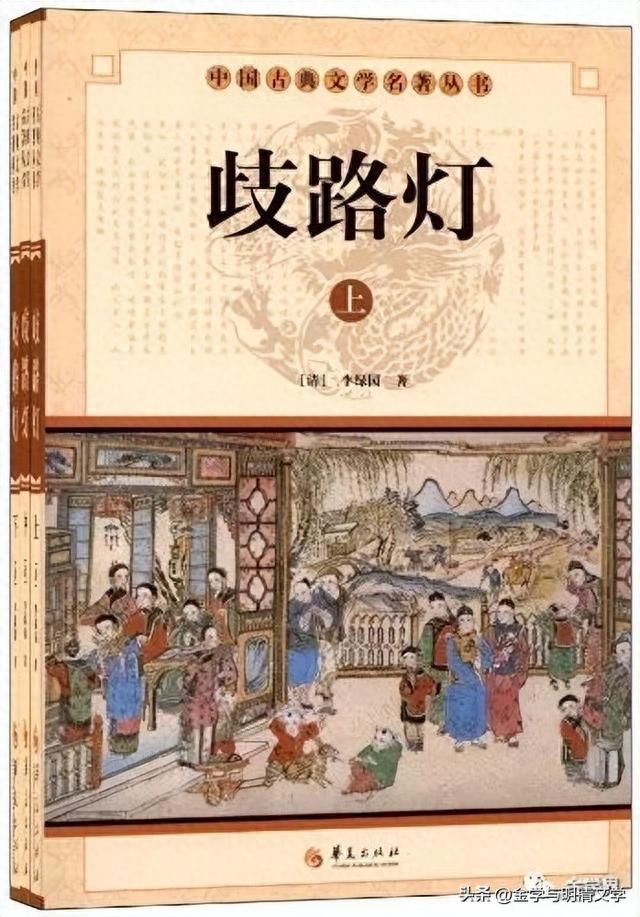
《岐路灯》书封
从《歧路灯》中可以看出李绿园所见到的《金瓶梅》正是当时在社会上通行的张竹坡评本《金瓶梅》。
书中第十一回写谭家塾师侯冠玉要用《金瓶梅》作教材,教学生以作文之法,他说:
那书还了得么!开口“热结冷遇”,只是世态“炎凉”二字。后来“逞豪华门前放烟火”,热就热到极处;“春梅游旧家池馆”,冷也冷到尽头;大开大合,俱是左丘明的《左传》、司马迁的《史记》脱化下来。
所谓“开口热结冷遇”,正是指张评本的第一回简目,“逞豪华门前放烟火”,正是指张评本所用的崇祯本第四十二回的题目。
《自序》还说:“坊佣袭四大奇书之名,而以《三国》《水浒》《西游》《金瓶梅》冒之。”这也是张评本的观点,张评本板心并题有“奇书第四种”。
在《歧路灯》第九十回说:“坊间小说,在《金瓶梅》,宣淫之书也……画上些秘戏图,杀却天下少年矣。”张评本所用之崇祯本正有插图二百幅。在《歧路灯》中,不但作者所鞭挞的反面人物受到张竹坡对《金瓶梅》评语的影响,连作者所褒扬的正统理学家也受到影响。
为人恂谨的“祥符优等秀才”苏霖臣就曾说:“《金瓶》《水浒》我并不曾看过,听人夸道,笔力章法,可抵盲左腐迁。”(第九十回)
张竹坡是清顺治、康熙年间人,乾隆年间正是张评本流行之时,《歧路灯》的描写是符合当时实际的。
李绿园还在《自序》中谈到他创作《歧路灯》是要发人之心,惩创人之逸志。
并且自诩说:“于纲常彝伦间,煞有发明。”在书中还表白:“草了一回又一回,矫揉何敢效《瓶梅》!”实际上他在《歧路灯》中的写作方法深受《金瓶梅》的影响。

《金瓶梅》书封
《金瓶梅》写的是明代万历年间的社会生活,却假托于北宋;而《歧路灯》也仿效之,书中写的是清代乾隆年间的社会生活,却假托于明代。
在这种障眼法之下,它们的作者都是以严格写实的态度真实地反映了各自的时代城市各阶层的生活。
《金瓶梅》写了西门庆的罪恶家庭由盛至衰的过程,重点写其盛;《歧路灯》写了谭绍闻的家庭由败而复兴的过程,重点写其败,这是由于作品的不同主题思想确定的。
但是两部作品都是以家庭生活为主线,把笔触伸向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写出了200多个栩栩如生的各式人物,上至缙绅豪吏,权贵宠宦,下迄帮闲篾片、僧优娼隶,三教九流,无所不包,堪称百科全书式的巨著。
如果说《红楼梦》是网状结构、《儒林外史》是连环状结构的话,那么《金瓶梅》和《歧路灯》都可以说是羽毛状结构。
只是《金瓶梅》有些细节比较粗疏有漏洞,而《歧路灯》在这方面则比较精细,针严线密,不但大的地理方位很少差错,就是书中的街道里巷也大都能和清代开封街道方位相吻合
读《金瓶梅》和《歧路灯》可以感到不少人物性格有相道之处,特别是那些妇女和市井无赖形象,如潘金莲和巫翠姐,泼辣尖刻,西庆和盛希侨的霸道粗俗,李瓶儿和孔慧娘的委曲求全,应伯爵和夏逢若的刁钻无赖等。
同时这些人物又在各自不同的典型环境中,显示了自己的典型性格特征,《金瓶梅》中的应伯爵“是个破落户出身,一分儿家财都嫖没了,专一跟着富家子弟帮嫖贴食,在院中顽耍,诨名叫做应花子”(第十一回);
《歧路灯》中的夏逢若“诨号叫做兔儿丝。他父亲也曾做过江南微员,好弄几个钱儿……到了他令郎夏逢若手内,嗜饮善啖,纵酒宿娼,不上三五年,已到“解矣’的地位。但夏逢若生的聪明,言语便捷,想头奇巧,专一在这大门里边,衙门里边,串通走动”(第十八回)。
由于他们的经历、地位相似,所以他们的行为也就有不少相似处。

《金瓶梅》第六十七回写黄四求西门庆到衙门中去替他说人情,“正说着,只见应伯爵从角门首出来,说:“哥休替黄四哥说人情,他闲时不烧香,忙时走来抱佛腿。昨日哥这里念经,连茶儿也不送,也不来走走儿,今日还来说人情!”及至见了黄四递上一百两雪花官银,立刻就变了态度,并力劝西门庆把银子收下,又说:
哥,你这等就不是了,难说他来说人情,哥你赔出礼去谢人,也无此道理。你不收,恰是你嫌少的一般,倒难为他了。你依我收下这个礼,虽你不稀罕,明日谢钱公,又是一个样儿。
黄四哥在这里听着:看你外父和你小舅子造化,这一回求了书去,难得两个多没事出来,你老爹他恒是不稀罕你钱,你在院里老实大大摆一席酒,请俺每耍一日就是了。
《歧路灯》中的夏逢若也有如此翻云覆雨的伎俩。谭绍闻被人赖胀讹诈,派人请他的把兄弟夏逢若出来作证。夏逢若觉得近来没得到谭绍闻什么好处,就对来人说:
咦!弄出事情来,又寻我这救急茅房来了?……我目下有二十两紧账,人家弄没趣,你回去多拜上,就说姓夏的在家打算卖孩子嫁老婆还账哩,顾不得来。等有了官司出签传我才到了。到那时只用我半句话,叫谁赢谁就赢,叫谁输谁就输。如今不能去。
可当他得知谭绍闻答应送他二十两银子,马上就去作证:
夏逢若把手一拍,骂道:“好贼狗攮的,欠人家ニ百多两不想拿出来,倒说人家扭了锁,提了戏衣。我就去会会他,看他怎样放刁!真忘八攮的!咱如今就去。想着不还钱,磁了好眼!”(第三十回)
从这两个无赖帮闲形象的塑造我们可以看出李绿园的创作受《金瓶梅》影响的痕迹,不过夏逢若形象的成功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它是来源于作者对社会生活的体验观察,所以作者不但能写出夏逢若与应伯爵相同的一面,也能写出其不同的一面:他为母亲跟着他受苦去世而痛哭;
他想起绍闻的好处,有时也不肯勾引绍闻继续堕落,还运用机巧威慑高利贷商人对绍闻的讹诈等等。通过多侧面的描写,创造了一个独特的“这一个”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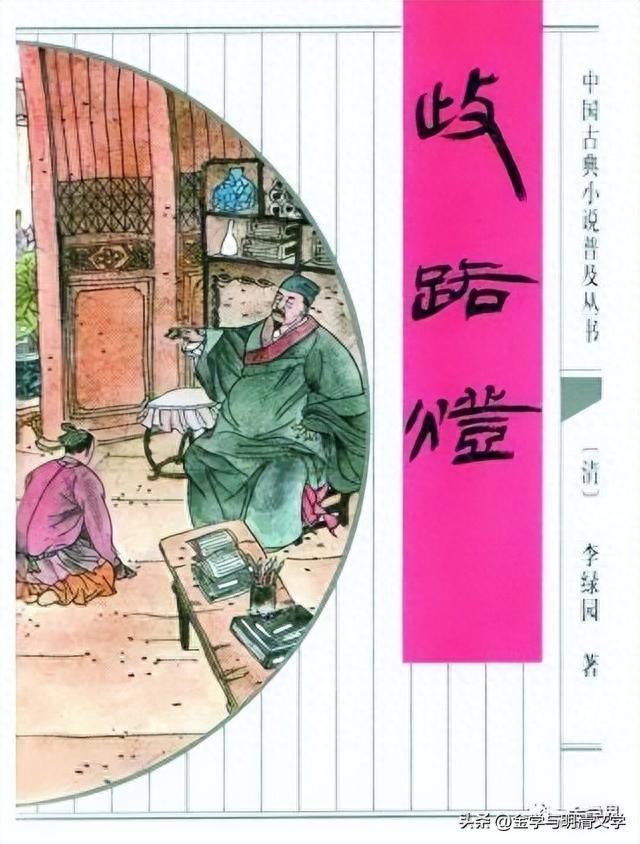
《岐路灯》书封
《金瓶梅》从第六十二回至第六十五回以细致的笔墨写李瓶儿丧事的全过程。
书中的主要人物都在此登台表演,作者还竭力铺排大出丧的豪华场面,以大手笔描绘了西门庆极盛时的气势,形成整部作品的高潮。
有趣的是,这一表现方法,《歧路灯》和稍后出现的《红楼梦》的作者都不约而同地运用在自己的作品中,孔慧娘大出丧和秦可卿大出丧各自成为这两部作品中的重场戏。
《歧路灯》从第六十一回至第六十三回,在作品的高潮部分铺排大出丧场面,成功地表现谭家油灯将尽,回光返照的局面。
在《金瓶梅》之前的白话小说由于主要供说话艺人演唱,所以特别注意人物的对话和行动,环境描写则较少。《金瓶梅》很善于通过庭室陈设等环境描写来衬托人物性格。
《歧路灯》也十分注意运用这一手法,第二十四回写谭绍闻来到赌棍张绳祖家:
只见一个破旧大门楼,门内照壁前,栽着一块极玲珑太湖石儿。……进的二门,是三间老客厅。绍闻见厅檐下悬着匾,心里想着看姓氏,谁知剥落的没字儿。
又转了一个院子,门上悬着“云中保障”匾,款识依稀有“张老年兄先生”宇样,绍闻方晓得主人姓张。进的门去,三间祠堂,前边有ー个卷棚,一副木对联,上刻着七言一联云:“一丛丹桂森梁苑,百里甘棠覆浩州。”
就在这曾是丹桂才士、甘棠贤臣的旧家祠堂中,不肖子弟张绳祖纠集一帮赌徒妓女玩乐。这很容易使人联想起《金瓶梅》第六十九回对林太太家的描写:
文嫂导引西门庆到后堂,掀开帘栊而入。只见里面灯烛荧煌。正面供养着他祖爷太原节度邠阳郡王王景崇的影身图,穿着大红团袖蟒衣玉带,虎皮校椅坐着观看兵书,有若关王之像,只是髯须短些。傍边列着枪刀弓矢。迎门朱红匾上“节义堂”三字;两壁书画丹青,琴书潇洒;左右泥金隶书一联:“传家节操同松竹,报国勋功并斗山。”
也就在这曾是节操松竹、功勋斗山之家,女主人勾引西门庆干着淫欲的勾当。这两处反衬手法的运用何其相似!

崇祯本《金瓶梅》插图
再比如《金瓶梅》第三十七回写和西门庆勾搭的韩伙计王六儿的房间:
……让进房里坐,正面纸门儿,廂的炕床,挂着四扇各样颜色绫段剪贴的张生遇莺莺蜂花香的吊屏儿,桌上拣妆、镜架、盒罐、锡器家伙堆满、地下插着棒儿香。上面设一张东坡椅儿,西门庆坐下。妇人又浓浓点一盏胡桃夹盐笋泡茶递上去,西门庆吃了。
《歧路灯》第五回写纳贿营私的布政司上号吏钱书办家:
……让进房里坐,只见客房是两间旧草房儿,上边裱糊顶槅,正面桌上伏侍萧、曹小像儿,满都是旧文移、旧印结糊的。东墙贴着一张画,是《东方曼倩偷桃》,西墙挂着一条庆贺轴子。一张漆桌,四把竹椅,……这钱书办取个旧文袋来,倾出茶叶,泡了三盖碗懒茶,送与二位,自己取一碗奉陪。
通过环境描写把人物的地位、心理、品性都一一展现出来。李绿园学习《金瓶梅》用庭室环境陈设来刻画人物性格是很明显的。
运用白描手法来描写人物神情,这是《金瓶梅》和《歧路灯》的又一共同点。不过这是我国古代小说的传统手法,这里就不再多作比较了。
需要指出的是《金瓶梅》喜欢对人物的面貌服饰做精细的描摹,这一点《红楼梦》学得很到家,而《歧路灯》则擅长略貌取神的方法,不注重肖像描绘。
在语言方面,《金瓶梅》《歧路灯》运用口语都十分纯熟,熔民谚、俚词、古语、歇后语于一体,语汇十分丰富,但《金瓶梅》近于讲唱文学,有些地方流于粗鄙、琐碎;《歧路灯》则更近于案头读物,有些地方不够流畅,有“掉书袋”的毛病,可读性比不上《金瓶梅》。
语言的特点也反映了作者一个在于暴露,一个在于劝诫的不同立意。
大约是李绿园对《金瓶梅》中的一片鬼蜮和黑暗的感触,也由于他从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文艺观出发,他在《歧路灯》中努力想写出一批正面人物和光明结局。
但他又恪守着已经处于僵死状的封建理学的道德去写这些人物,书中充斥着对礼教的赞叹,反映了作者落后的世界观。他力避《金瓶梅》的“宣淫”,使许多情节不能展开,削弱了作品的深刻性和感染力。
正像徐玉诺将《歧路灯》与《品花宝鉴》相比较后批评的那样:“李绿园对于下流生活到底是门外汉”,书中的妓女调情“是乡间小叔子及姑表姊妹的爱,并不是娼妓的本事”(《墙角消夏琐记》)。①
不过作者在描写那些正面理学人物时,尚能按照生活中的本来面目去着笔,使我们看到了理学家们的孤陋与伪善。而书中谭绍重整家业、父子具显的结局则只是作者一厢情愿的空想,是不真实的败笔。
连作者自己也叹道:“后半笔意不逮前茅,识者谅我桑榆可也。”(《自序》)
从以上简单地比较可以看出,《歧路灯》的作者不论从正面或反面,都努力从《金瓶梅》加以借鉴。
《歧路灯》是又一部在《金瓶梅》的影响下由文人独立创作的以家庭生活为题材的世情小说。

本文作者 张弦生 高级编辑
注:
①载《明天》1929年第二卷第八期。
文章作者单位:中州古籍出版社
本文由作者授权刊发,原文刊于《殷都学刊》,1989年第2期。转发请注明出处。
- 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