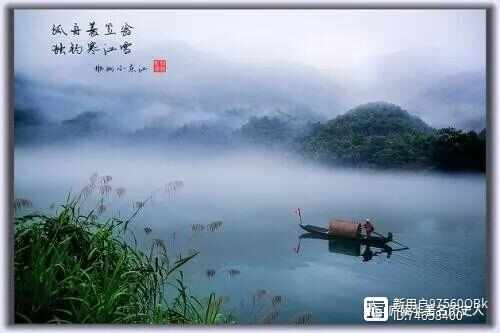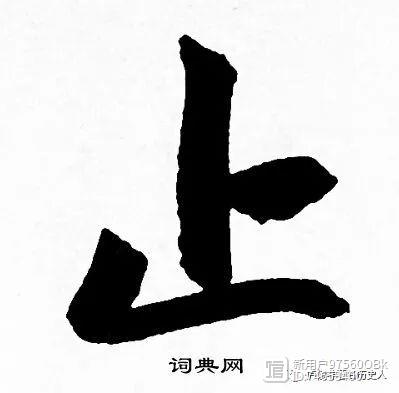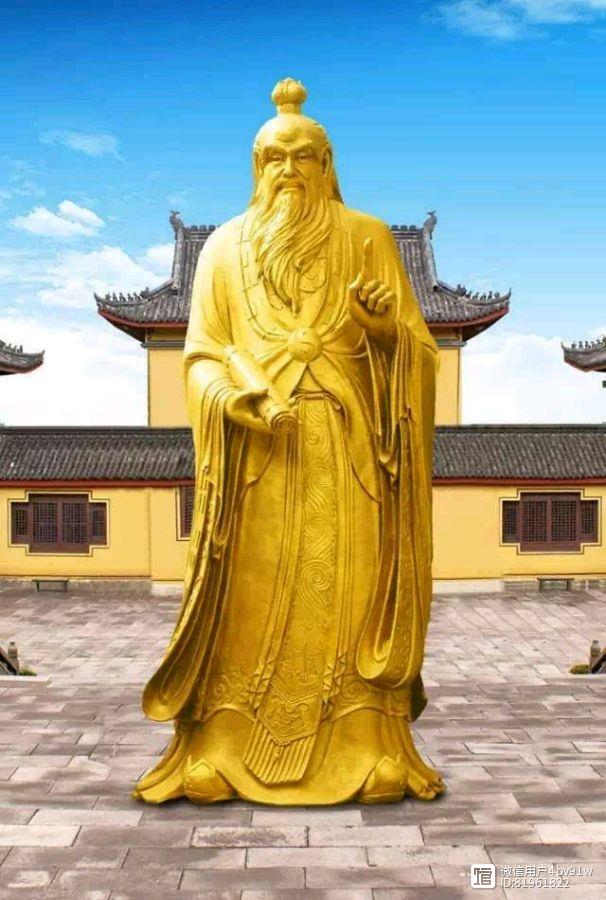庄子外篇《缮性》原文、注释、白话翻译和赏析
庄子外篇《缮性》原文、注释、白话翻译和赏析
开篇就提出不能用世俗观念修治人的本性,而应以“以恬养知”的方式修治人的本性。这也是本篇的中心议题。下面根据表述的内容分成三个部分,分别注释、白话翻译和赏析。
一、
【原文】
缮性于俗(1),以求复其初(2);滑欲于俗(3),以求致其明;谓之蔽蒙之民。
古之治道者,以恬养知;知生而无以知为也,谓之以知养恬。知与恬交相养,而和理出其性。夫德,和也;道,道也(4)。德无不容,仁也;道无不理(5),义也;义明而物亲(6),忠也;中纯实而反乎情(7),乐也;信行容体而顺乎文(8),礼也。礼乐徧行(9),则天下乱矣。彼正而蒙已德(10),德则不冒(11),冒则物必失其性也。
【注释】
(1)缮:修补、整治;性:指人的自然本性。(2)复:恢复;复归。
(3)滑:治,治理。“滑欲”与“缮性”为相对应词组。
(4)道:天理。(5)理:合理。
(6)明:《大雅·皇矣》传曰:照临四方曰明。凡明之至则曰明明。明明,犹昭昭也。(7)中:心中、内心;反乎情:反映到性情上。
(8)信行:恪守信用;容体:行为举止;顺乎文:合乎章法。
(9)徧行:执行偏差。(10)蒙:敛藏。(11)冒:鲁莽。
【译文】
用世俗的观念修治人的自然本性,为期求复归初始的状态;用世俗的观念治理欲念,为希望能达到明智;就叫做蒙蔽人。
古时修道的人,以恬淡涵养智慧;有了智慧却不使用,就叫作以智慧涵养恬淡。智慧和恬淡相互涵养,因而和谐与天理就由人的本性体现出来。德,就是和谐;道,就是天理。德无所不容,就叫做仁;道无不合理,就叫做义。义照临四方因而物类相亲,就叫做忠;心中纯厚朴实而且反映到性情上,就叫做乐;恪守信用、行为举止合乎章法,就叫做礼。礼乐执行偏差,那么天下定然大乱。持守正道,敛藏自己的德行,德行就不会鲁莽,德行鲁莽那么万物必将失却自己的本性。
【赏析】
开篇就提出不能用世俗观念修治人的本性,而应以“以恬养知”的方式修治人的本性。古代那些修道的人,修缮自己本性,都是以恬淡无为来涵养自己的智慧。虽然有了心智却不以心智妄为,仍是恬淡无为。这又是以自己的智慧来涵养恬淡无为。心智和恬淡互相涵养,由此和谐与天理就由人的本性体现出来。这就说明了恬淡无为和智慧在修治人的本性中的重要性。这也是应坚持的一项原则。同时还指出“以恬养知”要体现在“德、道、仁、义、忠、乐、礼”诸方面。并阐述了“德、道、仁、义、忠、乐、礼”的具体含义,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这一切只有顺应于天理,才能发挥在修治人的本性中的作用。像本来是雅正的音乐,如果礼乐偏行,不顺于天理,而世人偏于靡靡之音,则扰乱了人的德性,也就扰乱人的本性。
二、
【原文】
古之人,在混芒之中(1),与一世而得澹漠焉(2)。当是时也,阴阳和静,鬼神不扰,四时得节(3),万物不伤,群生不夭,人虽有知,无所用之,此之谓至一(4)。当是时也,莫之为而常自然。
逮德下衰(5),及燧人、伏羲始为天下(6),是故顺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农、黄帝始为天下,是故安而不顺。德又下衰,及唐、虞始为天下,兴治化之流(7),浇淳散朴(8),离道以善(9),险德以行(10),然后去性而从于心。心与心识知而不足以定天下(11),然后附之以文(12),益之以博(13)。文灭质,博溺心,然后民始惑乱,无以反其性情而复其初。
由是观之,世丧道矣,道丧世矣。世与道交相丧也,道之人何由兴乎世(14),世亦何由兴乎道哉!道无以兴乎世,世无以兴乎道,虽圣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隐矣。
隐,故不自隐(15)。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见也(16),非闭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发也,时命大谬也。当时命而大行乎天下(17),则反一无迹;不当时命而大穷乎天下(18),则深根宁极而待(19);此存身之道也。
【注释】
(1)混芒:混沌、迷茫。(2)澹漠:恬淡寡欲。
(3)四时得节:四季的变化顺应时节,即四季分明。
(4)至一:高度和谐一致。(5)逮:等到。(6)为:指治理。
(7)流:此指风气。(8)浇淳散朴:使淳朴的社会风气变得浮薄。
(9)善:作为、而为。(10)险:损害。
(11)心识知:心中所认识到的智慧。
(12)附之以文:附加上浮华的文辞。
(13)益之以博:指增加众多的俗学。
(14)何由兴乎世:以什么来振兴人世。
(15)自隐:自我隐匿:(16)见:显现;
(17)大行:指大道通行;(18)大穷:指大道难行。
(19)深根宁极:固守根本、深藏静处。
【译文】
古时候的人,处于混沌、迷茫的状态,一辈子都恬淡寡欲。这个时候,阴与阳谐和宁静,鬼神也不干扰,四季分明,万物不受伤害,有生命的东西都能尽享天年,人们虽有心智,却不用它,这就叫做高度和谐一致。这个时候,人人无为,天然自处。
等到后来道德衰退,到了燧人氏、伏羲氏开始治理天下,那时还顺应民意却不能和谐一致。道德再度衰退,到了神农氏和黄帝开始治理天下,那时安定却不能顺应民意。道德再度衰退,到了唐尧、虞舜治理天下,兴教化之风,使淳朴的社会风气变得浮薄,背离大道而为,损害德行而行,然后舍弃了本性而顺从于心中欲念。欲念用心中所认识到的智慧而为,不足以安定天下,然后就附加上浮华的文辞,增加众多的俗学。浮华文辞泯灭了道德的本质,众多的俗学淹没了纯真的心性,然后人民开始迷惑和纷乱,没有什么办法返归本真和回复初始的状态。
由此看来,人世丧失了天道,天道也抛弃了人世。人世和天道互相抛弃,有道之人以什么来振兴人世,人世又以什么来振兴天道呢?道没有办法在人世间兴起,人世没有办法让道得以振兴,即使圣人不躲进山林之中,他的德行也会隐藏起来。
隐居,并不是自我隐匿。古时候所说的隐士,并不是潜伏身形而不显现于世,并非缄默不言而不愿吐露真情,也不是为了深藏才智而不表露,是时遇和命运在大相背谬啊。当时来运转大道通行于天下,就会返归高度和谐一致之境而不显露踪迹。当时运不佳,大道难行,就固守根本、深藏静处等待时机。这就是保全自身的方法。
【赏析】
第二部分的内容,一是缅怀远古混沌时代人们的生活状态,这个时代,万物高度和谐一致,人人无为,天然自处。二是指出自燧人氏、伏羲氏治理天下开始,到神农氏、黄帝治理天下,再到唐尧、虞舜治理天下,历经不同时代,德行步步衰退,人世丧失了天道,天道也抛弃了人世。有道之人被迫隐居保全自身。自此,人类再也不能返归本真了。
在人类初期的原始时代,人的智慧、能力都极为有限,为求生存,不得不互相依赖,融融相处。随着时代发展,人的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和生存能力等逐步提高。在时代进步的同时,人们对身外之物的追求以及占有欲越来越强烈。人心越来越狭隘,私欲越来越膨胀,自然醇和的本性逐渐丧失。庄子对这一社会现象进行的批判是应该的,但是将其归罪于社会的进步就不应该了。妄想社会再倒退到人类初期的原始时代更是不可能的事情。在这种世道之下,为涤清世人的心灵提出缮性的主张,其积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三、
【原文】
古之行身者(1),不以辩饰知(2),不以知穷天下(3),不以知穷德,危然处其所而反其性已(4),又何为哉!道固不小行,德固不小识(5)。小识伤德,小行伤道。故曰:正己而已矣。乐全之谓得志(6)。
古之所谓得志者,非轩冕之谓也(7),谓其无以益其乐而已矣(8)。今之所谓得志者,轩冕之谓也。轩冕在身,非性命也(9),物之傥来,寄者也(10)。寄之,其来不可圉(11),其去不可止。故不为轩冕肆志(12),不为穷约趋俗(13),其乐彼与此同,故无忧而已矣。今寄去则不乐,由是观之,虽乐,未尝不荒也(14)。故曰,丧己于物,失性于俗者,谓之倒置之民(15)。
【注释】
(1)行身:处世立身。(2)辩:诡辩、巧辩。(3)穷:困扰、困窘。
(4)危然:独正不倚的样子。反其性:返归本性。
(5)固:本来。小行:指不识大体的行为。小识:狭隘意识。
(6)乐全:为保全天性而高兴。得志:得其快意。
(7)轩冕:原指古时大夫以上官员的车乘和冕服,后引申为官位爵禄,泛指为官。
(8)无以益:不再贪图别的利益。(9)性命:自然本性。
(10)傥 tǎng :同“倘”。傥来:偶然而来。寄:寄托
(11)圉yǔ:本义为养马的地方。引申为抵挡,防御,阻止。
(12)肆志:随心;纵情。
(13)穷约:困穷潦倒。 趋俗:与世俗同流合污。
(14)荒:荒淫无道。(15)倒置:本末颠倒。
【译文】
古时候处世立身的人,不用巧辩装饰智慧,不用智慧使天下人困窘,不用智慧使德行受到困扰,独正不倚地生活在所处的环境而致力于复归本性,又何须再做些什么呢!道本不是不识大体的行为。德不是狭隘的意识。狭隘的意识会伤害德,不识大体的行为会伤害道。所以说,端正自己也就可以了。为保全天性而高兴,就可谓得志了。
古时候所说的得志,不是指高官厚禄,而是指不再贪图别的利益自身快乐罢了。现在人们所说的得志,是指高官厚禄。高官厚禄在身,不是天然本性,是外物偶然到来,临时寄托罢了。既是寄托,它的到来不必阻止,它的失去也不必阻止。所以不可为高官厚禄而随心纵情,不可因为困穷潦倒而与世俗同流合污,高官厚禄与困穷潦倒,其间的快乐相同,因而没有忧愁之说。如今寄托之物失去便不快乐,由此看来,虽然曾经有过快乐,未尝不是荒淫无道。所以说,自身丧失在物欲中,本性丧失在世俗中,就叫做本末颠倒的人。
【赏析】
第三部分与第一部分相呼应,指出修治本性、恬淡与智慧相互涵养的的要求。其核心思想是“危然处其所而反其性已,又何为哉”,“正己而已矣。乐全之谓得志”。即独正不倚地生活在所处的环境而致力于复归本性,不须再做些什么。端正自己也就可以了。为保全天性而高兴,就可谓得志了,切不可做本末颠倒的人。
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名著《岳阳楼记》中的一句话说得好,即“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从语意上讲,是不因外物的富有,个人的获得而骄傲和狂喜;也不因为外物的丢失、损坏,个人的失意潦倒而悲伤。内在涵义是指无论面对失败还是成功,都要保持一种恒定淡然豁达的心态,不因一时的成功而兴高采烈,得意忘形;也不因一时失败而垂头丧气,妄自菲薄,无论何时都要保持一种淡然平静的心态,做到宠辱不惊。这是一种思想境界,表示了处世立身之人深远与豁达的胸襟。
- 0000
- 0000
- 0000